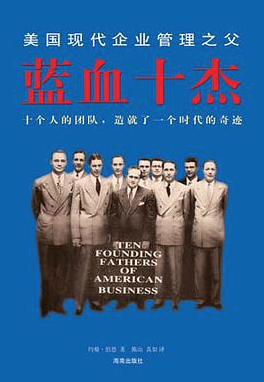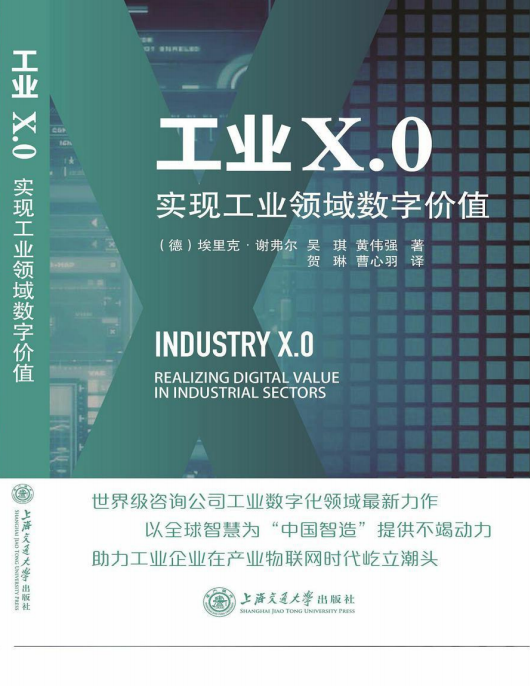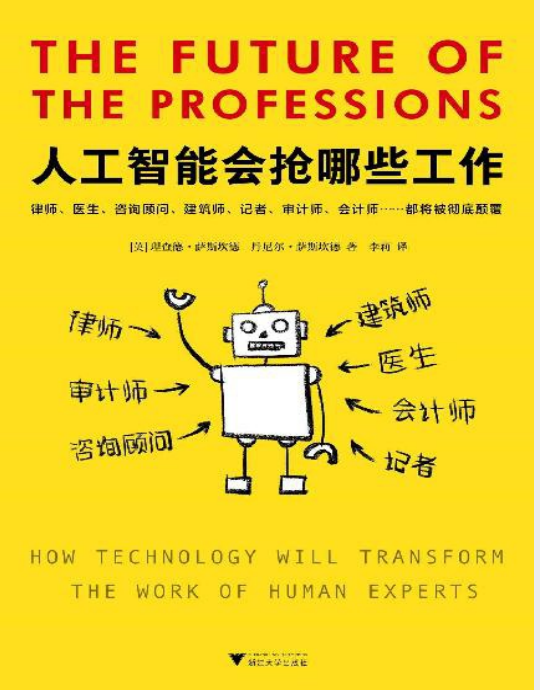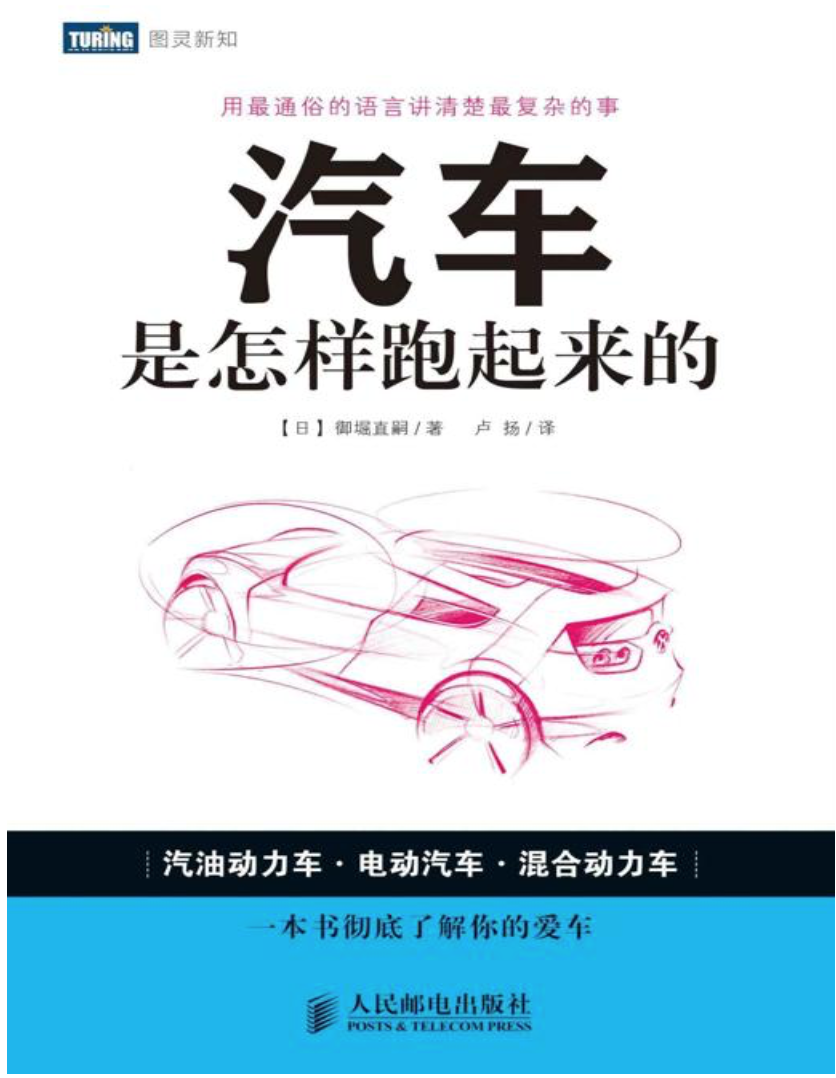12 十杰各自纵横
大部分的人都能轻松愉快地执行一份工作,但是却为头衔所困。头衔的作用是相当奇特的,它几乎相当于一块臂章,上头写着:此人除了自我膨胀,会贬抑其他人之外,无事可做。
——亨利·福特
在舞厅开门的数小时前,就有二千多人顶着滂沱大雨,淋得全身湿透,在纽约的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饭店的门前排队。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时值美国为间谍恐惧症所笼罩,而政客们正激辩着马歇尔计划的优缺点。当福特开着他那辆崭新的福特汽车从几个街外的卡尔敦豪邪开到华尔道夫时,这些事情在这一刻似乎都为他而静止。在那里,纽约市长保罗·奥代尔啪哒一声开了电源开关,把整个饭店的舞厅照亮得像是嘉年华会,为展览正式揭开序幕。
群众虽然全身湿漉漉却十分兴奋,把展示新车型的舞厅挤得水泄不通,连东、西厢的巴瑟顿厅、裴翠厅和亚斯德廊都为人潮所占据了。亨利·福特夫人从舞厅包厢的座椅上往下看,看着众人翘首引领,等着看她的孙子,其热切不下于他们想见新车型。四十多年前她就参加过第一次汽车展,她的丈夫把这个展览形容成“世界上最伟大的展览”。
在六天中有约二十五万人前来参观布里奇为打败通用汽车,而推出广受报界佳评的新车款。在如火如茶的工作及无时无日的开会检讨了六个月之后,他终于达成了目标。现在他为自己开一个足堪媲美恺撒大帝的庆功晚会。
新车上路
这是布里奇的大事。这个一九四九年车型和取代 T车型而起的 A车型造型上全然不同。这是布里奇的宝贝。以往挡泥板总是自方方正正的车身上悬挂而下,现在福特丢弃这个众所熟悉的模样,以更精巧的车身造型取代,挡泥板、车头和车尾的线条更平顺,没有多余的装饰。这型款式立即造成轰动。这款车型才在汽车商的展示屋正式揭幕的第一天,就有十万多人抢先订购。
然而对那桑顿小组留下来的七个人而言,这个新车型似乎不存在。他们并非对这个车型有了健忘证,而是他们给排除在计划之外。福特宣称这型车款花了公司一千万小时,七千二百万美金才生产成功。青年才俊们在福特所花的大笔时间、金钱中只占了极小部分。他们并未全心投入汽车的制造,而是投入公司的改造。财务控制、预算编列、生产进度、组织图表、成本和定价研究、经济分析和竞争力调查,占据他们全部的精力。
他们认为这个新车的款式或工程并没有突破,它的成就在于生产规划上。除了利斯外,他们没有任何人能像布里奇或克罗素一样,一跳进车里,立即就能对它的性能做一番分析。布里奇只要坐进车里十五分钟就能凭本能告诉你这车子是太重了还是太轻,它开起来的感觉是美妙还是糟糕透顶。触摸和感觉对青年才俊而言并非有用的观念,它们不是可以计算的观念,它们根本不是观念。触摸和感觉并不是改革的基石,也不能引导企业走向完美的道路。
就制造出一部他想要的车子而言,布里奇是成功了,但他并未真正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在他和青年才俊的差异后面,潜伏着一场美国企业未来的争斗。一边是为车子的美、声音、感觉和自由而活的汽车族,谈起引擎就眉飞色舞;另一边是像桑顿班底及日渐增加的支援部属这些人,快感对他们而言是来自控制组织中得到的,而非自一个从生产线上出炉的崭新车款。
在福特公司,这样的分裂并不消太多的争战,而是一个既定的结论。公司的困难和福特解决困难的企图,使得公司里的汽车族风光日子所剩不多。
企业组织
在福特公司,青年才俊变成专业人才。就像是外科医生对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不带感情一样,每个青年才俊都是冷静、理智而客观。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却是一九四九年的车让他们扮演起重要的角色。尽管布里奇急就章下设计生产的车型获得大众热烈支持喜爱,这款车的品质却是一场恶梦。这款车会漏水。车门常无缘无故地就自己开了。板金部分有凹痕。引擎常在开车中就熄了火。汽车的防震装置在车子一驶上崎岖的平交道就七零八落,工程师怪罪制造部门,制造部门怪罪工程师。总要有人为这整个产品担起责任。
先前,查尔斯·桑顿指派莱特、包士华、摩尔和安德森负责一项改革公司组织的计划,使它的权责划分更清晰。莱特以前一手创始了统计控制小组的组织图。福特采用了他们部分的建议,但并未彻底遵循,因为这个建造战后新车型的工作比组织事宜更重要。尽管如此,布里奇了解这事的重要,在他初次和桑顿见面时,他就建议桑顿和他的从属要读杜拉克的企业组织概念。
此书后来被视为一个里程碑,成为全球建构现代企业的蓝图。当时探讨经营这个议题的书相当少,即使有这样的书,也似乎不是为管理大众而写的。大多数的管理人员多半不知自己是在做管理的工作。
一九四三年,正当桑顿在华盛顿渐成气候时,通用汽车请杜拉克来公司研究它的政策和结构。公司里第一代的开拓者不是已经离职,就是马上要退休,皮耶·社邦,已经去职有二十年之久了。杜邦在二十年代接管通用时,公司处于形同破产的状态,是他将分权制度引进通用才改变了一切。阿尔弗雷德·斯隆,这位杜邦重用为总裁的专业管理人才,已经在通用公司担任企划暨总裁有二十年之久。在战争末期时,斯隆已届退休年龄,并打算辞职。多纳森·布朗,这位为通用设计财务控制,使得公司得以延续下去的人,计划和斯隆一起离职。公司希望它下一代的管理人员能有一套文字记录,作为他们的导引地图。
这个私人研究后来成为一本将管理转变成科学的书。诚如杜拉克自己所说,此书对所有主要的管理议题都加以剖析,许多还是创见:组织和社会责任;个人和组织间的关系;高阶管理的功能和决策过程;管理人才的发展;劳工关系、社区关系和顾客关系。
这是深奥难懂的东西,一个企业界的新“量子物理”,对老亨利而言毫无用处。在斯隆开始架构通用的组织时,福特汽车占有 55%的市场,而通用才占有 1%,老亨利对通用的这些改变大声嘲笑。在他的自传中,他如此写道:
“对我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比时人所谓的‘组织天分’这种心智偏向更危险的了。这种偏好之下所产主的通常是一幅巨大家谱模式的图表,上头画着权力如何分化成系统。家族树上结满了又大又圆的果实,里头写着某某人或某某氏的名字。每个人有一个头衔,受他所占的果实大小严格限制权责范围,对一个位在图表左下角的人言,如果他想转达一个建言给总裁或董事长的话,就得花去六个礼拜的时间,而且如果他真有幸层层上报到这些威严凛凛的长官,建言之上早就一路添加了无数的批评、建议和解释。”
如果老福特不需要组织的话,那是因为他要求公司的每一件事物都得一件一件地上达到他那里。但公司已经快速成长得像是一无人照管的花园,到处都长满了果实。福特所指的组织图正是通用起死回生,使公司的表现超越卓伦的原因。在一九四○年之前,通用已经占有了汽车市场的 45%,而福特的占有率下滑到仅仅 16%。依桑顿的分析,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九年,福特的产销只能勉强打平,通用却赚进上十亿美元。克莱斯勒,依通用的模式组织,也赚进了七亿多美元。
杜拉克所分析并公诸于世的观念将主宰接下来数十年的组织思考。大型公司由各个小公司般的部门组成,各个部门有一个实际负责人职司部门的独立运作。他们直接负责公司的营利问题。生产部门专事公司现有的企业经营,而职司公司法人阶层的人则负责公司长远规划。在推广这些观念上,斯隆并非是唯一的人。通用电子的拉尔·科迪诺也是这个运动的先锋,而在一九四五年之前,许多大公司,包括标准石油和 AT&T已经将他们公司的组织改头换面,恪遵分权模式。但是权责规范问题,就如福特所言,一直都存在。
分权自治
留在福特的青年才俊奉杜拉克的书如圭臬,因为他们在工作上所遇到的问题,书中都提过也讨论过。他们一致同意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树立起一个权责分明的组织体系,当他们在福特这个缺乏效率的庞然大物中摸索会诊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各个部门之上根本没有负责人。大部分大型公司都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负责人事,一个是负责生产。负责人事的人研拟规划公司的策略,检测它的成长进展以及做成决策并下达。负责生产的人则专司决策的执行。在福特却没有如此划分。一九四九年这款车的品质问题就反映出权责划分不清的毛病。
一度,桑顿把詹姆斯·莱特派到包士华在迪尔班旅馆的房间,专心一意地为福特彻底改组一事重新规划。这个任务是由亨利自己明确交待给他们的。“给我好好待在那里直到你把问题解决了,”桑顿告诉莱特。莱特离开圆形塔,在包士华的房间待上一个多礼拜,而后带回一份厚厚的报告,叫“福特汽车公可的组织问题”。因为报告的封面是蓝色的,他们遂管它叫“蓝皮书”。这份报告是一份有分量且令人赞赏的成果,有着五十七页的内文和图表,明确地叙述福特公司需要在操作上分权,在管理上集中。报告写得简明扼要,仿佛莱特知道福特二世需要完整又彻底的企业教育,即令他有布里奇在身旁辅导。的确,阿杰·米勒后来说,他宁愿向布里奇和福特个别做简报。“布里奇是一个真正的专业人才,”他回忆道。“你可以用三言两语就让他知道一大堆事。但是对亨利的话,你得先给他背景资料,然后再做报告。”莱特在报告里说组织的作用是建构一个引导企业事务的模式及一个蓝图。它为企业运作添了明确性、秩序性、以及目的性,没有了组织,企业运作就茫然混乱无所适从。
它避免工作的重复,行动的浪费和漫无目的的努力。它为成本的分配和控制,预算的编列,获利或亏损的衡量,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办法。同样地,莱特也为公司的每一个部门的分权做规划,包括设立一个福特分部。
每一个分立的部门各自负责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因为各自都有不同的作业;结果是各个部门都必需对获利与否负责。
成本随时可以独立计算出来,没有利润可言的活动可以随时找出,而管理上的决定,譬如说资金的运用以及产品的转换,可以按确实可靠的数字来订定。
高层管理人员可以免去例行公事的负荷,而有专心致力于他们的基本工作的自由——即计划、决策和控制。
如此就可以培养出全方位的行政人员;在操作层面上言,他们可以有更广阔的经验,而独立、主动及领导能力就因此培养出来了。
在福特公司,他们的主意立即就受到采纳,而这批人也急着推动。詹姆斯·莱特、查尔斯·包士华,法兰西斯·利斯写下详细的工作内容,将生产和幕僚作业分开,分解报告关系,确立公司里资讯和财务的流程。未经莱特和包士华的组织部正式登录记载,任何部门都不准设立。他们甚至还设计亨利和布里奇要用什么样的纸张为公司定下规矩,一份“政策函”——即任何建立公司政策的备忘笺——要写在绿色的纸上;而一份“行政函”——即任何公司副总裁的备忘笺——则用蓝色纸,好让它们在公司所制造上吨的文件中更加醒目。对他们而言,没有一样细节是不值得注意的。
新带头大哥
然而,在桑顿去职之后,这个小组立即有一个人和其他人保持距离。青年才俊很快就发现不管是什么团体,只要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的地方,不消片刻他就居上主导。查尔斯·包士华一点也不感讶异,因为当初他和在医院疗养时的麦克纳马拉初次会面时,他就见识到了。当时战事急转直下,麦克纳马拉受小儿麻痹病毒感染,桑顿来电命令从英国回到加州圣安娜中心的包士华去接替麦克纳马拉在派特森营区的指挥工作。
包士华马上为自己订了下一班飞机,飞到戴顿后立即到麦克纳马拉的病房报到。而麦克纳马拉呢,精神奕奕一如往常,坐在病床上,上头满布着空军文件。大部分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给探病的人叙述哪里出了问题,身体觉得如何如何。麦克纳马拉却没有,他意兴昂扬,只有一个速度——快速前进。
“哦,我很好很好,”当包士华问起他的病情时他这样回答。他根本丝毫未谈他的病况。包士华来的目的是要听麦克纳马拉扼要告诉他相关事宜,他好接替指挥工作,但麦克纳马拉无意把工作交出来:即使是在医院病床上,他仍要掌管一切。十天后,麦克纳马拉出院,而又再度回到工作。
他、蓝迪和米勒所做的和统计控制小组的情形一样。他们先设定好系统,让那些可供做财务控制之用的“事实”进入系统,然后藉由他们诠释数字的能力,掌控愈来愈多的实权。以往主计长基本上只是将所发生的事记录下来——他所做的是会计的职责,以及做财务记录。但是就如桑顿在空军所做的一样,麦克纳马拉为主计长规划了一个新关键的角色。在他们重新定义之下,这样的地位容许主计长从事计划,预测未来以及做数量分析。
这个新取向是受了像哈佛教授汤姆·桑德思、路思·渥克以及艾德·仁特极大的影响。渥克用“成本中心”和“预算中心”这样的词语,从这儿“利润中心”就自然而然诞生了。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幕后推动公司利润中心的设立,以为每个运作把脉。这些人超越传统的生产成本控制,把控制的观念运用到所有的事物,包括市场行销和采购。他们计算产品对福特而言“应该付多少”,而不是仅仅接受最可能的好价钱。
慢慢地,麦克纳马拉为美国企业界衍生出一套新术语和新规则。他在数字方面的鬼才令布里奇和克罗素赞叹有加,遂在一九四九年提名他担任主计长一职。他的快速爬升是由另外两位和麦克纳马拉一同形成“十杰”核心的青年才俊所组成的,米勒和蓝迪也拥有和麦克纳马拉同样的训练和理念。他们的晋升显示了一个主要的改变:头脑对企业的经营比狡诈更重要了。
MBA当家
在他们所承继下来的混乱中,最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是品管人员的缺乏。大体而言,福特的老将们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因为缺乏正规教育的关系,他们的才智无力使公司向前发展,而且他们对现状的改变有极深的怀疑。“我们无法重新训练那些管理财务方面的人,”米勒回忆道。“这些元老们已经习于他们以前做事的方式,他们再没能力去做任何改变。他们就是没这份能耐去修正适应。”
米勒认为这些财务幕僚是他所谓的“负面淘汰”的牺牲者。错误的人选以错误的理由受人延揽。他们移转到财务部门的原因是他们认识班奈特或其他福特的亲信,而不是他们有什么足以傲人的专长。公司从来不曾费心招揽米勒所称的“聪明小子”,就是那些在院校中名列前茅的人来加入公司。事实也如此,公司从不曾到校园去招揽人才。
麦克纳马拉、米勒和蓝迪——他们在哈佛、加大洛杉矶分校和普林斯敦攻读商学和经济——把这些老将革职,以年轻、心智相投、有大学文凭的人取而代之。财务部门逐渐成为福特公司内的知识圣殿,蓝迪比任何人都更投入,把招揽新血当成是他的主要计划和关注。
这位前任普林斯敦经济学讲师会亲自到几个主要企管硕士培训工厂哈佛、斯坦福、芝加哥、华顿、柏克莱和卡内基延揽最优秀的毕业生。当他到较不具知名度的大学去时,他从不会去考虑毕业班前二名以外的学生,蓝迪的想法是:这样的人和从名校出来的人没什么两样。他们之所以屈居那儿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更好的学校。在美国企业界还未盛行召募企管硕士之前,他早就开始如此做——当时他们多半被吸引到企管顾问公司工作。蓝迪一心一意要召募最优秀的人才,遂要求每一个财务人员每年固定负责召募一定名额的企管硕士到福特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演,更多的企管硕士加入财务分析师的工作,而他们的工作也更多。在福特把他的总部搬到美国路的玻璃宫之后,蓝迪的企管硕士——在海一般的灰色办公桌前辛苦工作——占去数层楼的办公室,也掌控了更大的权力。他手下的一名助理,口袋里带着一张小小的卡片记录着有多少哈佛企管毕业生在福特工作。每年都有数十名新进的企管硕士加入,直到财务幕僚增加到四百人之数,更多人在这方面担负起重要的任务。
这些因麦克纳马拉、米勒、蓝迪的关系而引进的庞大财务幕僚,不久就引发了一场从事制造生产和非从事制造生产者间的内战。这是一场介于相信底特律是汽车业重镇者和那些新进科技人员间的战争。随时序的推演,战争愈演愈烈,一场你争我夺下来,受到最大伤害的可以说是底特律自己。两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汽车族关切的是美国大众年年想有一款新车的欲望。数字族关切的是银行家和股东。两方除了各持己见外都无处可去,每隔一阵子就彼此大干一场。
新贵利斯
但在一九四九的早期冲突,克罗素赢得了桑顿极力想要的职位。令人感到嘲讽的是他的晋升却是在詹姆斯·莱特的分权自治实行的同时。这个福特公司内第二重要的工作,现由克罗素职掌,点子却是由他解雇的人所构想,而由桑顿的手下设计出来的。当亨利在走道上看到他,“喂,克罗素,”他说,“将来你就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实际掌门人。”
克罗素在获派此职之后,搬出了行政大楼,将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公司密得贝路上存放汽车零件的老旧库房。通用汽车的雪佛兰也做过同样的事,从通用大楼搬进公司的体育馆以节省成本。而那也正是克罗素的用意。利斯就是他召募来的第一批人马之一,他也找来了莱特担任他的个人助理,而后包士华职掌组织部。
克罗素是一个万事讲求仔细的人,对于那些直接向他报告的人,他都要求莱特准备他们的详细个人资料背景。这些履历资料得包括此人眷属的年龄,连他是否和他的妻子合法分居或者离过婚也要记录下来,或许克罗素认为这样的纪录显示此人的性格不定。克罗素是理想的公司警察,他甚至指导他的下属该如何写报告书才能为自己留下一道后路。“你不能说某件事情是如此如此,”克罗素说。“你得说,这事就表面上看来可能会有如此的状况发生。”
菜特发现克罗素好为人师。包士华也为克罗素对汽车业的知识所吸引。他总能够把一件在福待所出现的问题,引述他在通用汽车或费雪车身制造厂时所遭遇过的类似经验,作为他在福特新设立部门的助理,莱特常陪同克罗素巡视装配生产线,而克罗素就一边指示他该注意哪些事:像是焊接不良,车顶内部衬里有皱折或松垮。他知道隔音涂剂的正确使用方式,这是一种像沥青的隔音材料,生产线工人拿来涂在汽车接缝处,以阻隔金属间的碰撞,防止车子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那些负责涂抹隔音涂剂的工人的模样,令人难以置信,身上沾着这骇人的东西,裹了一层硬壳似的,活像史前时代的动物。如果隔音涂剂的涂抹不够精确的话,一部车开起来就会吵得要死,灰尘也会跑了进来,水也会经车体漏了进来。
后来,当桑顿打电话给莱特问他近况如何时,莱特都会提起克罗素,和他的工作是做得多么好。“哦,我的天哪,莱特,”桑顿就会如此回答他,他没法忍受这样的念头。他们一直都和桑顿保持联络,有时打电话,有时写信。
克罗素一定是感觉到了利斯是多么热中于他的工作,他变得十分喜欢利斯。当莱特让桑顿无尽懊恼地逐渐尊敬起克罗素时,没人比利斯和克罗素走得更近。的确,当利斯的第二个男孩在数年后诞生时,因为他们对克罗素的喜爱,遂把孩子取名为克罗素。在福特分部成立后没几天,克罗素就把利斯网罗来担任策划产品计划的经理。这份工作包括监督一部车从款式设计、打造到完成的每一个步骤。这份新工作、让利斯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处于对立的立场,因为担任主计长的麦克纳马拉,他的任务是要留心防止新成本偷渡加入,设法把能剔除的旧成本全都剔除。
这使得利斯成为克罗素的交通警察,负责管制所有进出他办公室的一切事务。他参予所有重要的会议,阅读所有重要的报告,研判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该搁置。这是福特企业中最大部门里的一个核心角色,而利斯在这个职位上,将有优异的表现。
连战皆捷
克罗素和利斯立即着手改进一九四九年的这款车。他们的人马把一部福特和雪佛兰拆解下来,把每一个零件放在工作台上,仔细比较,估测每一个零件的成本,哪一个的零件比较好、为什么,这个零件是否有待改进或更换。他们得力建立新装配厂进行游说,想出新的销售企划案,设计新车并进行制造。
克罗素和利斯立即着手改进一九四九年的这款车。他们的人马把一部福特和雪佛兰拆解下来,把每一个零件放在工作台上,仔细比较,估测每一个零件的成本,哪一个的零件比较好、为什么,这个零件是否有待改进或更换。他们得力建立新装配厂进行游说,想出新的销售企划案,设计新车并进行制造。
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合作无间——克罗素的精确和彻底,加上利斯给点子添翼、促销的鬼才,似乎是无懈可击。他们的目的一致,对抗财务控制的保守主义。
在上任没几个礼拜,利斯就接手负责福特的下一批新车。车子的计划已经获准,而它也含带着令人讶异的消息。公司建议拿掉八汽缸引擎,改采雪佛兰早就采用的造价较廉的六汽缸车款。中央财务方面的估计是八汽缸的生产要多花一百美元,再加上添加新机械的额外花费,因为当时的福特汽车只制造两种引擎。财务、工程和行销已经同意了这个改变。
利斯的一名助手却思·摩西,他曾在派特森营区的统计控制小组替利斯工作过,对这个改变提出质疑。早在一九二九年,当福特的.. A型车只有四个汽缸引擎时,雪佛兰就已经改生产六汽缸引擎。“那么他们就是喜欢汽缸罗?”福特叫道,“我就给他们八个看看!”这型车一推出,立刻造成轰动,为了它新增的快感,福特车成为年轻人、黑道人物和警察的新宠。大盗邦尼·派克是如此。迪灵杰还写了封信给老亨利,谢谢他的车子帮忙。他们一起去克罗素的办公室找他。
“克罗素先生,”利斯说,“你比我懂汽车业。但是我们认为福特不生产八汽缸引擎车的决定是一项错误。”
“我一直都买福特车,”摩西附和道。“我的第一部是一辆八汽缸引擎的,每个人都喜欢那个引擎的感觉。当他们在路上开着车时,它给了他们完全自主的感觉。福特和八汽缸引擎是一体的。他们晚上一同睡觉,早上一同醒来。你无法将他们分开。”
“你也看到了成本估价,”克罗素说。“它的成本太高。”
“如果我们失去了八汽缸引擎,”利斯说。“我们永远无法追得上雪佛兰。如果采行的话,我们还可能多赚一些。我无法相信说多两个汽缸会增加多少生产成本。”
克罗素眉头一扬说,“当我还在通用汽车时,我一直认为我们是疯了才会在雪佛兰上只摆六汽缸引擎。我认为你们的建议有道理。让我去见见布里奇先生。”
布里奇根本不喜欢这个点子,但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给克罗素的人马九十天的时间去搜集资料来佐证他们为何主张生产八汽缸引擎的车子。因此利斯就受派去搜集资料来反驳财务部门的数据。他和摩西访问了几个主要的汽车经销商对这个新改变的看法。到目前为止还未曾有人为这件事费心去和经销商讨论过。他们一致地希望保留这个高马力的引擎。利斯和摩西接着更仔细地检查财务部的数据,并到各个销售、产品企划、机械和制造部门追踪估价。他们发现到这个一百美元的估价是几个从通用汽车招募来的新进人员所计算出来的。八汽缸引擎的实际造价成本只比六汽缸引擎的贵上十六美元而已,但是福特却可以此为选择配备而多索价一百美元。那样一来就可以降低基本车型的造价,但同时保有公司与众不同的特色。利斯用新证据说服了公司,而事实上大多数的客户都选择了较高的马力,让福特赚饱了荷包。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班·米尔斯坐在克罗素的办公室里,他才从一次全国性马拉松式的钢铁和玻璃厂考察之旅回来。他最近才接任福特在堪萨斯城的新飞机制造厂的助理。克罗素力促他接下这个职务:“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不要分文接下这个新缺。”当电话响时,米尔斯才刚从迪尔班回来要和克罗素商谈这个生产行动。
电话是布里奇从巴黎打来的。他和亨利以及其他福特的高级主管在巴黎近郊的布瓦西的法国福特分厂考察。这个分厂的财务亏损连连,单单一九五二这年就预计要损失二百万九千美元。
在过去的四年来,这里的业务是由一名风度翩翩的法国人法兰斯·雷依德所主持。根据布里奇回忆,布里奇告诉克罗素说他要詹姆斯·莱特来接替雷依德,担任福特法国分厂的总经理之职。布里奇喜欢莱特,认为他有才干,每个礼拜日都和他及他的家人在布伦菲尔德的克兰布鲁克的教堂见面。但是克罗素推荐利斯接任,他告诉布里奇说利斯是他所有的人手中能力最好的一人。
“这个职务他能胜任吗?”布里奇问道。
“是的,他能胜任。他大概是你所能找到的最好人选。”
听到克罗素这边的谈话,米尔斯察觉出克罗素保荐利斯出任此职的弦外之音。他觉得克罗素由衷地不希望利斯离开福特,但又如此欣赏他而不愿耽误他的前途。
“好吧,”布里奇道,“谁来出任对我都是一样的。把他送上飞机,让他这个周未就来这里。他可以在礼拜六或是礼拜日抵法。今天才礼拜三而已。”
十杰小组逐渐失去它的团队色彩。福特公司这边还剩七名的原始成员。但是麦克纳马拉、米勒和蓝迪已经自团队中脱出,在财务部另组小队。莱特和包士华留在福特分部和克罗素共事。米尔斯则四处做着不同的工作,赢得打击问题专家之名。而现在利斯要到巴黎走马上任。桑顿、安德森和摩尔早已各走各的阳关道。他们的友谊无形中转薄。随着各人即将迈入三十好几之龄,各人愈来愈为自己、为成功、为权力而活。过往的一切和同济之情似乎成为不必要的包袱。现在重要的是什么事都要快,而速度不需要什么情谊牵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