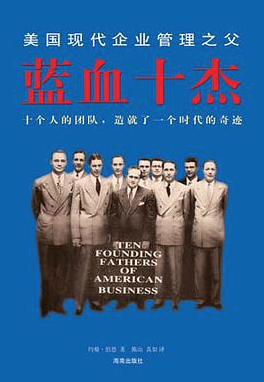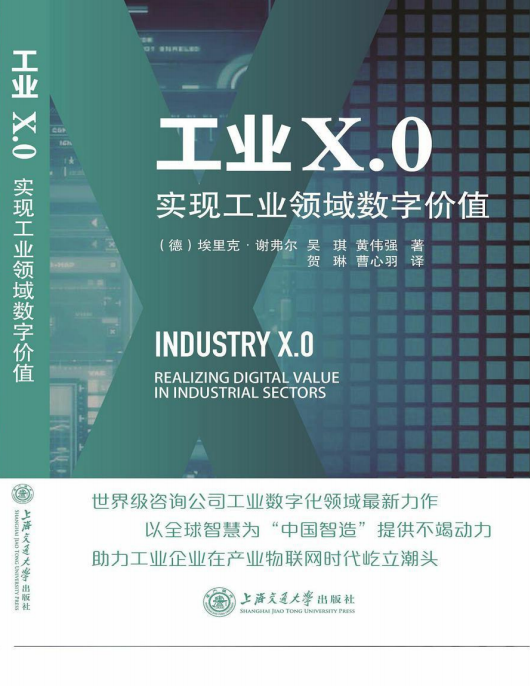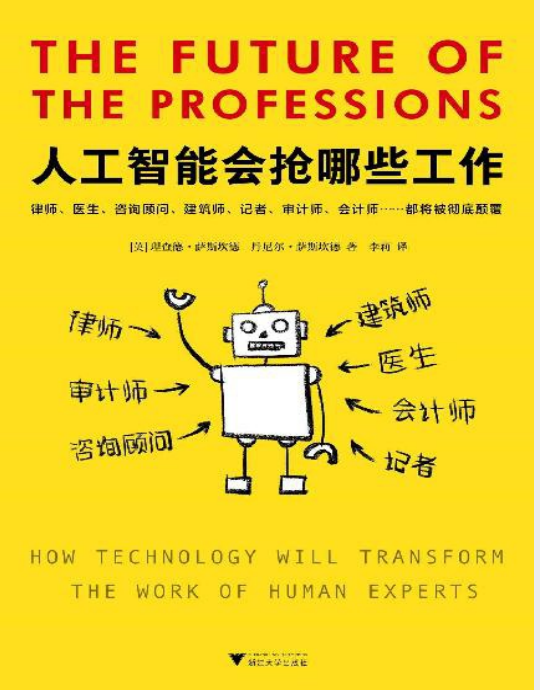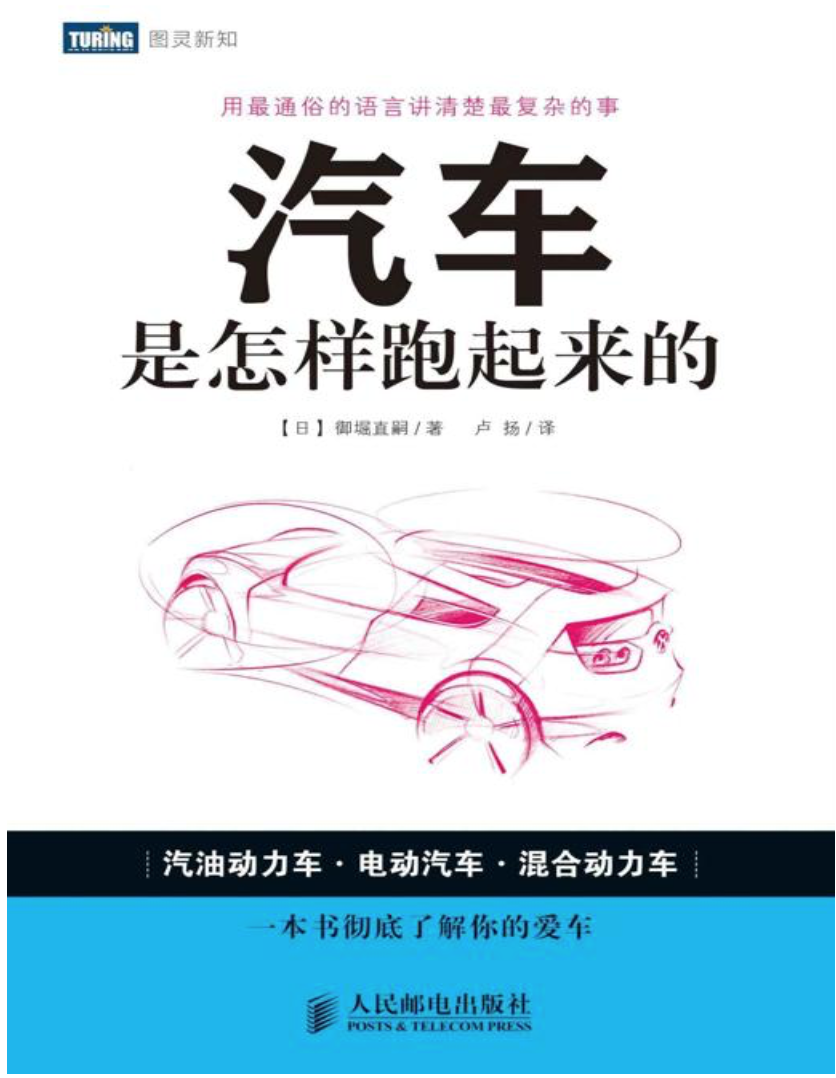第二章 从先锋说起
在这章里,我们来换个角度。
让我们带着大家浏览不同的专业群体,看看他们身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其中大部分都是技术导致的。我们将要呈现的内容,可能比较宽泛而且很不一样,但并不复杂。它只反映了部分地区的情况,尤其是英美国家,而且只是某一个时期——21世纪第2个10年的中段(2015年左右)。在未来的几年里,当我们回顾这些内容,通过敏锐的后见之明,毫无疑问会发现,我们遗漏了某些极好的案例,而大篇幅描述了一些应当被忽略的案例,甚至有些样本已经不复存在。这些情况都可以被预见到。想要全面穷尽地调查专业工作方面的技术变化,需要增加好多篇幅,还需要拥有超自然的精准度,才能找出最终的赢家。
但是如果我们纠结于这些特殊情况——成功、失败、遗漏——那我们在这章里,甚至整本书里想要表达的意思就被曲解了。借用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话来解释,我们所寻求的是透过表面这些涟漪,通过广泛研究选定的那些专业工作,来理解表面以下我们所感受到的深层次的变化。
2.1 医疗
埃里克·托普(Eric Topol),一名心脏病学家以及基因学教授,在《未来医疗:智能时代的个体医疗革命》(The Patient Will See You Now)一书中预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时代,每个人类个体都会拥有他们各自的医疗数据,以及计算机能力去处理这些数据……从出生到死亡……甚至在疾病发生前能够加以阻止。”也有许多其他的评论家做出了类似的预测。这样的未来和目前医生所采用的历史悠久的医疗手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传统的做法是,当人们觉得自己的健康出现问题,他们会进行预约,亲自拜访,和专家面对面单独进行一次或多次互动,然后通常由专家决定需要采取的行动,病人照单实施之后便离开。这种看似稳妥的手段所面临的最主要困难在于它不再那么让人负担得起。部分原因在于,受益于理疗保健行业的过往成就,人类的寿命正变得越来越长,长期健康护理的成本很高,人们得到治疗但并不能得到治愈。以英国为例,癌症、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长期护理需求占了总体医疗社保支出的70%。在医疗领域内,一个公认的观点是从业人员可以通过互相学习来使工作更有效。因此我们接下来将要讨论的是,医疗研究的刊物广泛存在,使得内科医生可以基于别人的研究和实验结果获得进步。尽管标准的协议和程序每天都被用到,而且它们的功效已经得到证实,但据阿图·葛文德说,医疗专业工作者仍然对使用简单的核查清单带着强烈的矛盾情绪。随着互联网的进步,病人依靠自身力量可以获得的健康相关信息比原来要多出许多。NHS Choices和WebMD network这样的平台提供了大量的症状和治疗手段方面的指引——每个月后者都有惊人的独立访问数量(1.9亿次),这些人并没有选择向全美国那么多医生去求助。各种专门的搜索引擎,诸如BetterDoctor、ZocDoc以及Doctor on Demand,让人们得以在一百多万名医生的数据库中进行筛选,有些情况下还可以看到类似于亚马逊风格的基于用户体验的评分。2014年,所有的英国病人首次能够查看37种关于普通诊所的不同数据库,并且会收到所有的特定风险警示(被称为普通诊所情报监控,Intelligent Monitoring of GP)。基础的症状检查在网上被免费提供给用户,并且网站可以立刻提供诊断结果,不需要任何外部的人为介入。
在线下,我们也看到了更加强大的计算机诊断系统。比如说纽约的伊丽莎白文德乳房诊所(Elizabeth Wende Breast Clinic),该诊所发现使用特定算法进行乳房X光检查可以使乳腺癌误诊概率下降39%。IBM的人工智能系统,被大家叫作沃森(Watson,更多信息见4.6章节),正在被应用到辅助癌症诊断以及推荐治疗方案上。它还被用于开发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治疗方案。设想一下,如果2014年每天新发布的医学文献中的2%和某个医生的工作相关,那每一天这个人都需要至少花费21小时去阅读这些文献,并持续一整年,而平均每隔41秒,一份新的论文就被发表了。因此沃森被寄予厚望,因为它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些资料的阅读,并且能够实时了解新发布文献的内容。目前,《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49%的读者认为实证医学是“失灵的”,而这些新系统可能就是一种重新帮助人类建立信心的方式。人们如此缺乏信心是有道理的——延误的、遗漏的、错误的诊断据说高达10%~20%。
在帮助医生诊断之外,医疗系统的其他方方面面也看得到计算机系统的身影。
美敦力公司(Medtronic, Inc.)设计的胰岛素泵和他们的心脏起搏器的方向是一致的——趋势是让胰岛素的剂量控制变得自动化,这种控制将基于传感器得到的数据,而不是专家的意见或者手动干预(不久以前,心脏起搏器正是如此工作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有一个药房,只有一名机器人在那工作,至今为止已经开具了超过200万个处方,并且没有出过一次差错,与此相比,美国的人类药剂师出错的概率大约为1%(相当于每年3700万个错误)。大约140家医院正在使用自动机器人TUG,它可以自己穿过走廊,发放很多物品,从纱布到药品,目前这些机器人每周发放5万次物资,节省了护士和搬运工的时间。全美半数医生都在使用一个叫作Epocrates的应用,这是一个数字化的药品信息核查系统,通过计算机来查找不同的药品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这一任务曾经非常耗时,通常要拿一本超过2500页的药品信息手册——《医生桌上参考手册》(Physicians' Desk Reference)进行手工查找,而且也不一定查得到。
除了医学应用之外,医学研究工作也开始仰仗计算机。IBM和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共同研发了KnIT系统(“知识集成工具包”, Knowledge Integration Toolkit),负责扫描现存的医学著作,并且为特定的研究项目生成新的假设前提。例如,以肿瘤抑制蛋白“p53”为例,对一个新的研究员来说,他得花费38年来消化7万篇关于“p53”的相关医学文章,但如果用KnIT扫描了这些文章,包括上百万篇其他的文章,再对扫描结果进行筛选,就能快速发现六个潜在的新化学“开关”——可以激活“p53”并让它发挥作用——而到目前为止,全人类总共只发现了33种“p53”的激活方式。沃森这类人工智能系统的愿景之一,就是确保普通情况下病人不再需要医生,只需要配备合适的诊断设备和掌握治疗规划工具的护士就足以够用。这种方式下,大量具备高度医学知识的工具都能够为护士所利用。换个角度,在这些系统的帮助下,“助理医师”足以治愈病人,这是一种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下的新的职业类别,他们接受过医药培训,但又没有传统内科医生学习得那么深入。尽管对于这些“助理医师”存在一些争议,但他们的出现,证实了常规的医学职业边界不再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了。现在医疗机构中的护士,已经被允许做一些小手术,而且他们开处方药的权限也在逐渐变大。
“远程医疗”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这种做法使用互联网视频连接,用以开展远距离医疗工作。如果需要进行远程放射检查或者远程皮肤病检查,不在传统医学中心的专家可以提供24小时的紧急图像处理服务;如果使用远程中风平台,心脏专家并不需要在病人身边,也同样可以进行紧急诊断,迅速提供建议。此外,远程手术技术也正在快速发展,通过高级机器人的协助,身处美国的外科医生团队可以取出一个身在法国,距离6000公里以外的女病人的胆囊(被称为林德伯格手术,Operation Lindbergh)。这一类技术都由“远程监控”和“远程诊断”设备提供支持。比如说,美敦力的远程监控网络Carelink Network,这一技术让心脏病患者能够将他们心脏设备收集的数据报告发送给医生,每个报告都相当于一次当面拜访。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也有一个远程医疗办公室,2014年使用了相关技术向超过69万名老兵提供了健康护理,而在通常情况下,退伍军人是一个地理上非常分散的群体,其中55%的人住在郊区,缺少接受传统医疗服务的便利。在英国西约克郡的Airedale,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使用思科网真技术(TelePresence)为数百个家庭养老项目提供护理支持,并且实验性地将监狱囚犯的医疗收治人数降低了50%。通常情况下,这些设备的存在形式往往与传统专业服务截然不同,非常令人难以想象——比方说谷歌和欧洲的诺华制药公司(Novartis)联手开发了一种“智能隐形眼镜”来监测血糖水平,替代了原先需要戳破手指提取血样的方式(测试、管理糖尿病的传统方式)。不得不说,“移动医疗”的市场也正在迅速成长,数以万计的设备、系统、应用程序搭建在现有的移动技术上——传统电话、智能手机、移动网络。这些设备和系统有着各式各样的复杂性。举例来说,BlueStar系统能够将智能手机变成具有经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糖尿病管理系统的设备,向病人提供个性化的治疗建议,并向医生提供实时的数据流。一个EyeNetra智能手机外接设备的成本大概只有几美金,其功能是一个可移动的眼部测试器件,功效和我们所熟悉的几千美金一台的验光设备一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截至2015年,全球大约有5亿名智能手机用户安装了医疗应用。移动医疗还有更简单的用法。试想一下病人可能会忘记医生所提供的医疗建议中的40%~80%,真正回忆起来的内容还有一半是错误的,然后另一半的病人忘记按照医生的处方吃药(在美国这意味着每年可避免1000亿美金的医院治疗成本)。考虑到种种不靠谱的状况,给病人发送简单的文本信息提醒(也给医务工作者)有效地改善了医疗效果。这也解释了GlowCap 小药瓶盖这样的设备为何能够获得成功——通过无线芯片监控药物的使用,发送提醒给健忘的服药者(它会闪光、发出哔哔声,然后发送短信),发送服药数据给医生,并且当药物需要补充的时候发送通知给药剂师。
数字设备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医疗领域,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再借助高级的系统,可以产生可观的研究成果。例如梅奥诊所发明了一系列算法,称为“嗅探器”(sniffers),它通过分析病人的实时数据来预测并警示潜在的健康问题。通常,这类数据流的规模需要动用大数据技术(见4.6章节)。再比如位于亚特兰大市的埃默里大学医院(Emory University Hospital)和IBM共同研发重症监护病房的床头监测设备,可以10个数据点每秒的效率收集分析每个病人的信息。如今许多新型设备和系统的成功商业化,引发了“自我检测”和“自我跟踪”的文化运动。这种现象被称为“量化生活”,成千上万的用户使用着这类设备,如Jawbone、Fitbit以及MyFitnessPal,来收集大量的个人信息——从脉搏数据到消化模式,从睡眠情况到心情状态——它们对数据进行分析的精细程度可以媲美许多临床医生。这些设备,设计的时候结合了审美元素,被称为“可穿戴设备”。更有甚者,成立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普罗透斯数字健康公司(Proteus Digital Health)正在研发一系列可穿戴设备的“升级版”——“可摄入设备”,一种小型药丸状的体内侦测设备,可以让病人吞下去,而且不需要电池驱动(用胃酸来提供动力)。
大型的网络社区也在逐渐兴起。在PatientsLikeMe网络社区里,30万人互相连接,分享各自的状况(目前大约有2300种不同的状况),交换各自的经验和治疗手段。据说脸书网也正在准备推出类似的线上“互助社区”。实际上,除了病人之外,全美超过三分之一的医生都已经使用Sermo网络来发布研究项目、临床案例以及互相交流;还有同样比例的医生使用有着类似功能的QuantiaMD网络。据统计,美国超过半数的医生是另一个专门针对医生群体的社交工具Doximity的会员。医药行业同样也在使用众包概念,面向大量的个人来收集想法和获得协助。在CrowdMed网站上,人们发布他们的症状,利用2000名在线医生——“医学神探”,把诊断方案众包出去。在InnoCentive上,医疗机构可以通过提供在线报酬,招募世界各地的人帮助他们解决所面临的医学难题。在Watsi社区,那些需要医疗救助但无法负担的人们,可以使用在线众筹平台获得捐赠。3D打印技术也在改变着现代医疗行业,它使许多医学项目成为可能,从铸型到假肢到牙冠牙套,都可以量身定制然后按需打印。外科医生还可以通过扫描病人的某些部位,打印相应的模型,在真正实施手术之前在模型上加以练习。打印的物体也不再局限于无机物,维克森林大学医学中心再生医学协会正在取得进展,他们试图制造一台机器来直接在烧伤病人身体上打印人体细胞。研究人员也在打印完整器官的路途上缓慢前进着,这非常重要——平均来说,每天,美国有21人、英国有近3人,死于缺少可移植的器官。对某些领域来说,依靠日渐强大的计算机能力,之前停留于理论想象阶段的一些实验逐渐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基因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通过分析病人的DNA来个性化定制治疗手段,预测未来可能罹患的疾病。2007年时,分析一个人类的基因需要花费大约1千万美金,到了今天,一次分析的花费只需要几千美金。如果不需要全面专业的基因分析,23andMe、Navigenics、deCODE这些公司提供的商业化测试,报价更是低到99美金起。在“基因编辑”领域,科学家致力于找到有问题的基因,主动进行干预去改变或者消除它们;纳米医疗技术(Nanomedicine)正试图将纳米技术运用到医疗领域里来。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费曼七十年前曾预言过我们有一天可能会“吞下外科医生”,这一预言已经成真——已经有微小的纳米机器人能够在我们体内游动、拍摄体内图片、运送药物、精准定向攻击特定的细胞,这些才能让最高明的外科医生都自叹不如。(在谷歌的研究基地之一谷歌 X里,据说这个项目也正在研究之中。)
除了计算机之外,制造技术也将在医疗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工程师正在开发大量精密的机器人系统来协助病患(有时被称为“辅助型机器人”)。比如,有的机器人可以帮助截瘫患者走路;有的机器人受病人控制,替代病人的四肢,发挥假肢的作用。有些系统能为医疗从业人员提供帮助,例如Cyberdyne公司制造的“混合辅助肢体”(Hybrid Assisted Limb),这种辅助肢体实际上是一套机械外衣,它就像一套延展骨骼,成本不到2000美金,但能够让护士借助它举起和搬运比他们自身承重能力大得多的重量。除了负重辅助之外,机器人同样也被用于医疗社交领域(通常被称为“社交辅助型机器人”, Socially Assistive Robotics)。PARO是一个治疗型机器人海豹,它能激励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并为其提供安慰——目前被纳入NHS的部分地区正在尝试使用它。由英国赫特福德大学的研究员设计的Kaspar,被用于帮助有自闭症的小孩。在“情感计算”方面(见4.6章节),科学家和工程师正在努力开发一种系统,试图模仿人类具有同情心的陪伴举止。在日本一家私人医院里,大多数房间都配有它们自己的机器人护士,它们不仅仅帮忙负重,也负责给每个病人提供陪伴。此外,社交辅助型机器人甚至不需要是实物机器人,一些智能技术也能够通过网上平台提供服务,比如AI Therapy平台,它为社交恐惧症患者提供个性化定制的虚拟治疗程序的系统,整个过程中,无须任何人工介入。
2.2 教育
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保持几个世纪没变了。一小群学生集中到一个物理空间,由一位老师进行现场教学,每一堂课设计成差不多同样的长度和节奏,遵循着相对精确的课表,老师扮演着“讲台上的圣人”。“一刀切”的做法针对着所有人,课堂上所讲的内容如果学生有什么不明白的,就需要自己进行探索学习,或者干脆就不懂到底;那些提前理解所教内容,希望进行下一步学习的学生通常则不得不耐心等待。
如果机构都拥有充足的资源,足够多的智慧才华兼备的老师和头脑聪明的学生,这种传统模式可以交出杰出的答卷。但是,只有极少数幸运者享受到了这种美好的结果。总的来说,许多发达国家里都没能提供足够的可负担的、高质量的教育。在各个国家内部,人们担心教育成果参差不齐,而对于整个西方世界来说,他们的教育体系正在输给其他国家,比如说印度。
过去,在教育中对技术的利用是不太常见的——也许会在教室的后面放一台孤零零的计算机或者在教室前面装一块电子白板,时不时地用互联网做一些研究,但也就仅此而已。相比之下,在“混合式”的学校里,技术却是处于核心地位的。Rocketship Education是美国加州九所特许学校组成的一个网络,学生每天花四分之三的时间和老师一起待在教室里,剩下四分之一时间在“学习实验室”里使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学习。在这个实验室里,软件会基于每个学生个体的情况针对每个学员的特定需求和实际能力来量身定制学习项目——教学内容、方法以及节奏——如果有学生要求特别关注,系统会发送提醒给老师。纽约的New Classroom学校、底特律的Matchbook Learning学校以及洛杉矶的Ednovate学校也都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这些学校使用的是“自适应”或者“个性化”教学系统。现在至少有70家公司提供这种系统:Knewton、Reasoning Mind、DreamBox都是其中比较知名的平台。它们正在向传统的“一刀切”教育方式发出挑战。通过个性化定制每个学生所能学习到的内容,他们在追求的其实是大家渴望但负担不起的“一对一”的教学方式——给予每个学生不同的关注。这也被称为“智能教学系统”。他们尝试解决的是已经困扰人类30年的“两个标准差问题”——一个普通学生如果接受一对一辅导,他将来的表现可能超越98%去普通课堂接受教育的普通学生(这大约等同于领先于普通课堂学生“两个标准差”,或者“两个西格玛”)。这种一对一模式,本质上,从19世纪开始就被牛津和剑桥大学加以应用并且被证明行之有效了。
在互联网上,有不同的网络教育形式。社交网络Edmodo,被称为“教育界的脸书网”,已经拥有超过5300万用户。这些特别定制的平台为老师、学生以及家长提供了互助社区。也有媒体平台,比如说Edudemic、Edutopia、ShareMyLesson,人们在这里分享他们在课堂上的经历经验(博客、视频、教学计划等)。还有“学习管理系统”和“虚拟学习环境”,例如Moodle,拥有超过6500万用户,BrightSpace拥有超过1500万用户,这些平台能够帮助老师组织教学、分发材料、在课堂外与学生互动。
其他在线平台提供教学内容。例如“可汗学院”(Khan Academy),它提供5500个免费的教学视频(被浏览过4500万次),提供10万个练习题(被解答了20亿次)。2014年每个月都有超过1千万的独立访问者——比2010年增加了70倍——这里学员的有效出勤率比整个英国的初高中学生的有效出勤率还要高。TED,集合了许多在线演讲(每场的长度大约为18分钟),这些有想法的演讲者的选题非常广泛,截至2012年底观看次数已经超过10亿次了,TED-Ed则基于这些演讲视频再建立起相应的课程。YouTube EDU,是整个YouTube在线视频网站的一部分,是专门为教育类内容所设立的,它收纳了超过70万高质量的教育视频——而它们只是发布在这个网站其他地方的、未经雕琢的但同样有用的视频资源中的一小部分。
这些在线平台的设计结构各不相同,但学生通常都是使用平台来跟上教学进度或者寻求学业进步。有些老师则利用平台来寻找教学材料,用于传统方式的课堂教学。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让世界顶尖专家直接与学生对话呢?还有人使用这些工具来改变教学方式,比如说直接翻转课堂教学形式,让学生回家在平台上观看常规的课程讲解,相反把做作业环节放到课堂上来。父母用这些平台来实现“在家教学”,小孩子在家接受教育,他们不上传统的学校,最近这种现象在美国数量激增,比1999年到2012年间所占整体学龄儿童的比例翻了一番。这种种平台都依赖着像可汗学院的创始人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这类人的强大个人魅力,他们从无到有亲自制作每一部视频。除此以外,即使是目前已经储备了丰富知识积累的机构,也在采用类似的平台分享专业知识。比如说2011年,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大学校长都说明他们提供网络课程。
在过去几年里,这些课程的性质和规模发生了改变。一系列“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s)相继面世。这种在线课程,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通常是免费或者收取的费用很低,很少听说存在上课人数限制(至今为止,某一课程报名人数最高达到过30万人)。在Coursera这由两位斯坦福大学教授创办的在线平台上,以及在由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创办的EdX上,来自上百所机构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为百万名学生创作并且交付了数以千计的MOOC。比如说,单单一年内报名哈佛MOOC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哈佛建校383年以来所接纳的学生总数。在 Udemy和Udacity这样的平台上,甚至不仅仅是学术性的任何专家,其他人也都能够主持、运营一堂MOOC。而且这些平台还被用于辅助小型的传统课堂教育,被称为“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S),回归到之前提起过的“混合式学习”形式。
人们也在对在线工具进行试验,看是否能够进行不同形式的学习成果评估和认证。例如,对于那些提供MOOC课程的老师,用传统方式批阅成千上万学生的作业是不现实的(这些老师平均每周花9小时在批阅传统教育的功课上)。有些系统使用“同伴互评”的方式,让学生们互为其他同学的功课打分,另外有些使用“机器评分”的方式,基于一些算法把评分过程完全计算机化。Degreed和Accredible之类的平台用这种方式来为课堂外所做的功课打分和进行认证。这类平台和系统基本上都可以在便携式设备上使用,它们使用教育类应用程序作为补充。2015年初,在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里,教育类程序是第二大流行的类别(排名仅次于游戏)。美国天使投资人约翰·杜尔(John Doerr)曾经预测,2014年全球教育类程序的安装数量将达到7500万。这些应用程序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从针对学生用户的自动更新的电子教科书和测试材料,甚至到类似ClassDojo那种帮助老师管理不守规矩的学生、和父母保持沟通的工具。随着越来越多的学习在数字平台上开展,数据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与大数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Learning with Big Data: The Future of Education)这本书里,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I nberger)以及肯尼思·库克耶(Kenneth Cukier)描述了传统教育中所使用的为数不多的数据点——测验成绩、报告卡片、出勤记录等——在庞大得多、精彩得多的数据集面前是如何黯然失色的。丰富的数据被收集起来,从学生点击了屏幕哪个位置,到学生回答一个问题花了多长时间。而且成千上万个学生的信息都可以被收集、存储起来。一门新的学科——“学习分析”,正在试图解读收集到的这些信息。分析这些信息的目标是为了给学生和老师提供更好的反馈,进而可以优化“个性化”“适应性”教学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案。很多平台对它们所收集的知识和研究提供开放式访问。有些事情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以至于我们甚至忘记了它们刚出现时是多么具有颠覆性。以维基百科(Wikipedia)为例,每个月有大约5亿人浏览这个收藏了3500万篇文章的资料库,大约69000名主要的在线贡献者负责创造并更新其中的内容,总共有超过280种语言版本,不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曾经的百科全书,一经印刷就开始过时,内容分为多卷,装帧精美,价格高达数千英镑,对比之下就显得特别古旧。目前有超过1万个开放式访问的在线学术杂志,收录了超过170万篇文章,通常都是经过同行审阅过的,但是在网上阅读、复制或者发送都不收取任何费用。截至2017年,盖茨基金会(每年支出9亿美金研究经费)将只资助那些愿意把研究成果以某种形式免费提供给公众阅读的学者。传统的订阅方式是昂贵的——有着全球最大的教育基金的哈佛大学,在2012年已经宣布它的图书馆无法负担那些传统期刊的订阅费用了。有各种各样的商业和收费模式支持着这些服务。有些是完全免费的,有些设置了付费门槛,有些是现成的商品,有些则是开源数据库的。Duolingo是一个免费的在线语言学习系统,它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模式——要求学生翻译从大段外语内容中摘取的小部分外语文字,这些文字来自于其他公司付费让Duolingo翻译的内容(CNN和BuzzFeed用它来翻译新闻故事)。这个平台同时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免费的在线语言学习工具,又提供收费的翻译众包服务。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家庭教师、讲师都面临着挑战。社会不再那么需要“讲台上的圣人”,更为需要“身边的向导”,因为他们能够帮助学生浏览各种专业资源。新的角色和新的学科会出现,例如教育软件设计师负责搭建“适应性”学习系统,内容管理者负责编辑管理在线内容,数据科学家负责收集大量的数据集并开发“学习分析”来解释这些数据。因此当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前校长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认为“接下去25年里,高等教育将发生的变化要超过之前75年的变化总和”时,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另外前唐宁街顾问迈克尔·巴伯爵士(Sir Michael Barber),在他所写的《一次雪崩正在来临》(An Avalanche is Coming)中(书名恰如其分)也预测了教育界将面临的巨变。
2.3 法律
在《法律人的明天会怎样:法律职业的未来》(Tomorrow's Lawyers)里,我们预测过司法行业在“接下来的20年里将经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巨变将超越过去整整2个世纪的变化程度”。无数评论家都同意,法律专业即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事实上,律师和法官的工作惯例从英国作家狄更斯时代到现在,基本没发生过多大变化。这一延续至今的架构在全世界都差不多,无论是协助解决纠纷,为交易提供建议或是为客户的权利与义务提供咨询。法律建议由服务于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人工定制而成,通过一对一形式提供,交付物为文件文档(常常是长篇大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这种咨询服务基本以小时为基础计费收费。随后,各方集合在一个专门为此建造的法庭里,由一位公正的仲裁者,采用正式的程序以及历史积淀下来的各种流程,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企图解决人们的争端。除了律师以外,其他人都非常费力地试图弄明白状况。
目前这一传统模式所面临的最大压力就是成本。狄更斯本人可能过度夸张了问题,他说法律文件是“堆成山的昂贵的胡说八道”,但大多数法律和法庭服务的确变得让人无法负担,无论是个人消费者还是全球性的商业客户。
目前,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法律市场已经开放,所以律师不再对法律工作享有垄断地位。无律师资格的人士可以拥有、运营法律业务,同时律师事务所也可以在股票交易所公开上市发行股票或者从私募基金等机构进行外部融资。这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市场。研究表明,几乎三分之二的个人,相比较传统的律师事务所,更愿意选择接受商业街上的品牌公司的法律服务。英国合作银行(Co-Op Bank)宣称他们将在350个银行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法律服务,另外其他知名的非法律业务企业,比如英国电信(BT)以及英国汽车协会AA,也已经承诺要开始提供日常的法律服务。传统的律师“独唱”正在受到威胁。
新的服务提供方已经加入到商业法领域中——像Integreon和Novus Law这样的法律流程外包方,像汤森路透这样的综合咨询机构,以及大量出现的“替代性商业机构”。最后提到的这个群体,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得到2007年颁布的《法律服务法案》的授权,并由Riverview Law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他们用低于传统律师事务所的固定费率来雇用并使用具有资质的律师。
法律业务的另一条成长路径是自由职业律师所形成的网络。始于2000年的Axiom是其中的领军典范。自从那时起,不同的律师事务所都开始使用类似的方式,大部分通过和前雇员签署协议来完成合同约定的服务。例如,英国博闻律师事务所(Berwin Leighton Paisner)的“按需提供律师”(Lawyers on Demand)以及英国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Pinsent Masons)的“Vario模式”(一群自由职业律师所组成的网络)。
总体来说,大的律师事务所正在成立新的劳务部门来应对成本压力。律师们把法律工作分解成更加基础的任务,寻找替代性方案来完成那些更加日常和重复性的工作,比如说法律文件审阅、尽职调查、日常性的合同起草,以及基础的法律研究。这样一来,有些法律事务被外包甚至离岸外包,交给律师助理,打散分包,然后向客户收取固定价格。有些领先的律师事务所已经开始着手构建他们自己的低成本基础服务设施了。此外,针对企业所面对的新课题——法律风险整体管理,整个法律行业也采取了许多行动,基本精神在于“避免争端要好过解决争端”,此外认可法律只是整体服务的一部分,律师将和会计师、咨询顾问、税务专家一起为客户提供整体专业服务。技术在律师执业转变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除了高度普及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尤其是电子邮件、会计和文件处理软件等),以及完善的法律搜索工具(例如万律网Westlaw和律商联讯LexisNexis),许多不同的新系统正在把律师的工作变得更加系统化,有时甚至会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在众多系统中有一个重要类别,它们的主要功能是系统化地生成法律文件。这些“文件汇编系统”——基于ContractExpress和Exari工具构建——通过和用户进行简单互动沟通后,能够自动起草生成高质量的文件。一开始这些工具主要为律师服务,现在类似的在线系统正在逐步向外行人士开放。法律行业中还出现了其他的文件相关工具。例如,Docracy收集了各种法律合同并向公众开放;Shake帮助人们在手持设备上创建法律合同,现在还可以直接从网上获得法律帮助。尽管非法律人士通常认为通过国家网站或者非营利性网站,研究大量实用的、通俗易懂的、各种法律领域的指导对他们帮助更大,但澳大利亚许多地区的法律和判例法都可以免费查阅到了,它的实际意义要比国家网站和非营利性网站提供的指导更有价值(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澳大利亚法律信息协会所做的开拓性工作)。商业性的在线法律服务,例如LegalZoom和Rocket Lawyer也在生根发芽逐步成长,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更为复杂的专家诊断系统,可以应对情节复杂、跨地区的法律问题,并且能够做得比一流专家更好。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Allenhehe&Overy)已经开始提供这样的服务,也有年轻得多的法律服务供应商,像Neota Logic,正在推出能够处理复杂规则并进行深度推理的系统。
律师事务所和客户之间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各种线上的交易资料室共享信息。这些都是基于互联网的协作平台,可以方便地存储和取用跟交易或争端相关的文件。为了准备一个诉讼案件,需要审阅大量法律文件并从中选择最为相关的信息,此时智能搜索系统比初级律师和法律助理表现更为出色。大数据技术为系统提供支撑,无论这是一项专利纠纷(Lex Machina的服务)还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一次裁决,此类系统能够比诉讼专家更精确地预测庭审判决的结果。法庭也开始受到根本性的挑战。法律专家开始质疑法院所提供的到底是一种服务还是一个场所;产生纠纷的人和机构是否真的需要集结到一个实体法庭上来解决他们的纷争。一个替代性选项就是虚拟法庭。这种形式已经用在从容易受到攻击的证人身上采集证据或者为刑事案件进行预审,它的形式和传统的法庭没什么两样——律师、涉案各方或者证人——通过某种形式的视频接入出席。另一种变化形式是在线争端解决机制(ODR),最近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ODR提案得到了高等法院院长,也就是最高民事法官的支持,他认为这是“民事司法体系历史上激动人心的里程碑”。借助ODR解决争端的流程,特别是形成解决方案的过程,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完成——小到市民之间的口角以及大到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矛盾。举“在线仲裁”为例——这是eBay用于解决每年数量惊人的6千万个交易争端的ODR技术之一(是美国法院系统一年受理的案件总数的三倍多),这些工作都在一个被广泛使用的ODR平台上完成,它叫作Modria。另一个在线解决方案是Cybersettle,网络版的“在线谈判”系统,它处理过超过20万起个人伤害保险理赔,理赔金额接近20亿美金。此外,免费的在线服务系统Resolver,也已经帮助英国消费者向超过2000家机构申诉他们的不满。在线法律社区正在兴起。Legal OnRamp系统起初为主要的律师事务所和他们的客户提供社区服务,然后非法律人士逐渐开始参与出谋划策,分享自己在解决法律问题过程中的实践经验,最终形成了我们称之为“法律经验社区”的综合平台。技术改变法律行业的另一种发展方向是,把法律要求更好地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去创造价值,比如说把自动遵守健康与安全法规的模块整合到建筑设计中去,比如一旦温度超过某些法定水平,建筑能够自动识别应对。这样一来,人类不需要知道这方面的法律,也不需要进行主观判断来照章办事,这样就应该可以避免律师的介入了。
即使是需要使用律师的场合,人们选择使用哪位律师也不再纯粹依赖传统的口碑了。在线信誉系统开始取而代之,用于传播客户对于某个特定从业人员或者律师事务所的评价(比如说Avvo,拥有将近20万名美国律师的客户评价),比价系统(既有按小时计价的,也有按项目收费的),以及网络服务,就像Priori Legal,能帮助用户寻找合适的律师。长期来看,法律服务的未来不太可能像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美国畅销书作家、律师、政客)那样,或者法庭的鲁波尔(Rumpole of the Bailey, BBC播过的一部法律题材电视剧人物)所演的那样。我们的研究表明,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传统律师在很大程度上被先进的系统取代,或者在技术以及标准流程的帮助下被更廉价的劳动力所取代,甚至外行人士都可以通过在线自助工具取代他们。
2.4 新闻
早在19世纪,油墨报纸已经成为除了和亲密朋友、同事和家人交谈以外,许多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窗口。现在在许多地方,报纸的重要性正在降低。美国的报业,通常被视为其他以印刷为基础的传统行业的风向标。用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和约翰·尼克斯(John Nichols)在《美国新闻业的存亡之际》(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一书中所说,传统报业正在面临着“自由落体式坠落”。从2004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人均日报发行量跌落了32%。在同时期,期刊的印刷本数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广告收入已经回落到最初有记录的1953年的水平(经过通货膨胀调整之后)。英国报纸《卫报》(The Guardian)和《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的编辑最近被问到是否考虑停止印刷他们的报纸,收到的答复是:“他们认为使他们继续印刷的方法,是由他们的报社买下最后一些印刷机器,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在传统印刷报业极具萎缩的同时,在线平台开始繁荣起来。2008年,美国人第一次认为他们的新闻来源中,互联网(40%)的贡献高于报纸(35%)。2013年这一数据(新闻来源中互联网的占比)上升至50%。在英国,2010年至2017年间,通过互联网获取新闻和杂志的人口比例增长了一倍多(从20%上升至55%)。在冰岛这一数据则已经高达90%(北欧其他地区这一数据也十分惊人)。更为年轻的群体,也就是那些未来的新闻工作者和读者们,通过互联网(不再依赖报纸)获取新闻的比例更高。
传统报纸和在线平台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它们的命运也是息息相关的,反映出了深层次的、长久以来对老式印刷模式的不满。过去30年里,人们花在阅读报纸上的时间已经急剧缩水(减少了差不多一半)。然而,大部分的下降其实出现在2000年以前,也就是互联网普及之前。某种程度上,这是电视经历了历史性发展成为了主流新闻来源所造成的,不过这一情况也开始改变了。2013年,在全美50岁以下的人群里,互联网已经超越电视成为主要新闻来源。结果就是,传统报纸的业务模式出现了危机。曾经,报纸的存活主要依赖印刷物的广告费,再加上本身的销售收入(尤其是地区性报纸),但是如今广告预算已经转移到在线平台上,因为它们可以更有效覆盖更广泛的人群。当印刷发行量下降之后,报纸的销售收入面临压力。虽然大多数传统新闻集团仍然选择印刷市场,他们整合现有的业务,发行新的印刷刊物,以不同的形式和定价进行各种尝试。但公司也搭建了新的数字平台,将印刷的内容转移到线上。除了印刷报业公司之外,广播公司也在做类似的变革。然而,传统印刷和线上版本的成功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在英国,《卫报》的印刷发行量跌落到了英国11种日报里的倒数第二,但与此同时,它的网站独立访问人数却是全世界英语报刊类网站中第二高的(2014年9月超越了《纽约时报》)。
目前,传统印刷报业的商业模式仍缺乏清晰的替代方案。从收入规模来说,数字广告仍然只占到报纸收入的一小部分(2013年,这一数字为9%)。尽管人们在尝试许多创新的支付机制,从付费专区(某些内容需要付费订阅才能进入),到小额支付(阅读每篇文章需要支付一小笔费用)等。然而,截至2013年,仍然只有约十分之一的人为在线新闻支付了费用。通过平板设备发布的内容被寄予厚望,但距离真正成功的盈利模式仍然十分遥远——2011年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尝试发行只有iPad版本的报纸——《日报》(The Daily),结果不到两年就失败了。
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对在线新闻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脸书网(拥有超过13.9亿用户)、推特(2.84亿用户)以及YouTube(超过10亿用户)。其中半数的用户使用这些社交网络来与其他人分享新鲜的故事、图像和视频。无处不在的移动设备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连上网络使用这些平台。比如说,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BBC网站30%~50%的访问量来自于移动设备;2014年底,《纽约时报》网站超过一半的访问来自于移动设备,而且这一数据“每个月都在增长”;目前,YouTube网站一半的浏览都来自于移动设备,而脸书网每月用户中超过85%来自于移动端。传统的新闻集团使用这些平台来传播他们的内容。2010年在推特上,人们互相分享的链接中的四分之三都来自于“主流新闻”网站。许多记者个人或专栏所拥有的关注人数要超过他们为之撰稿的印刷版报纸的订阅人数。BBC突发新闻(BBC Breaking News)的首页所拥有的关注者(1390万)甚至超过整个英国印刷日报的发行量(750万)。有一次脸书网调整决定用户所接收到的新闻的算法,这使得本来拥有“惊人的流量”的《卫报》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流量出现了大规模下跌。所以,在今天,一个新闻网站是否能够得到社交网络的重视和关注是至关重要的。传统机构其实只是整个新闻生态圈中的一小部分。个人所构成的网络(自由职业者、活动人士、普通人)也开始通过一些线上系统(脸书网、推特、YouTube等)来创造和分享他们的原创报道和评论。这种所谓的“公民”“参与性”或者“自己动手”的新闻报道,以及支持这些形式的博客平台,在原先相对闭塞的传统机构主导的新闻世界里,加入了来自群众的振聋发聩的声音。Bleacher Report是一个由200位体育迷所撰写的博客,如今这个博客每个月有2200万个独立访问,这一访问量足够匹敌Yahoo和CNN的运动板块了。Global Voices,一个拥有1200名作者和编辑(多数都是志愿者)的网络,可以在互联网世界里努力搜寻、过滤、翻译(30种语言)各种主流媒体以外(他们称之为“公民与社会的网络”)的文章。斯科特·格兰特(Scott Gant)新书的标题正体现了这一改变的精髓——《如今我们都成了记者》(We're All Journalists Now)。新的“专供数字版本”的机构也已经出现,不断颠覆着传统的业务模式。《赫芬顿邮报》是一个营利性的在线新闻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在线上提交文章,一些作者还能领取到薪酬。《赫芬顿邮报》成立于2005年,在短短6年内,其月度独立访问者的数量就已经赶超了《纽约时报》。ProPublica由桑德勒慈善基金会所赞助,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的在线新闻编辑室,他们唯一的工作内容就是进行调查性报道。这一网站自2007年成立至今,已经获得了两个普利策奖和一个皮博迪奖。Buzzfeed是一个营利性的在线新闻平台,通过在线广告(以及风险资本)来维持运营,在2013年,其月度独立访问者数量也超过了《纽约时报》。总结许多这类在线平台的成功,我们发现社交媒体的作用至关重要。具有颠覆性的新兴技术还包括:Vox的“解释性”新闻,The Marshall Project的“公众兴趣”新闻,Real Clear Politics的“新闻聚合”, FiveThirtyEight的“数据新闻”。事实上,标题不仅对于被报道对象来说越来越重要,对于如何报道一个新闻也越来越重要。《赫芬顿邮报》的编辑对于同样的文章,会在不同的读者身上同时测试几条不同的新闻标题,来寻找能够创造最多阅读量的标题(所谓的A/B测试)。提供媒体网站实时数据的在线系统Chartbeat,则通过在简单的界面上展示新闻标题,使用户更容易看到网站最高阅读量的网页是哪个、流量来自于哪里等信息。
除了传播方式外,新闻的形式也在发生着改变,在各个平台上都可以看到,为新闻文字匹配视频素材的情形越来越多了。这是合乎情理的——2013年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都在网上观看视频。1995年,当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预测未来的报纸会变成一种“电子”报纸——“DailyMe”,新闻的标题和内容都会反映读者的特定兴趣时,人们认为他十分激进,好像“新闻公司乐意让所有员工听你差遣,来为你专门确定某一个发行版本”。然而仅仅20年后,这种个性化的新闻已经随处可见。Flipboard是一个在线平台(有9000万用户),它创造了一种“个性化的杂志”,新闻都按照读者社交网络的活动所归纳得出的兴趣来定制;脸书网新闻(脸书网 newsfeeds)和推特新闻流(推特 streams)全都是从一个用户的朋友那里筛选得到的内容或者他们选择关注的内容。当然,这一技术也存在着争议,因为这一技术会采用特定的算法,决定将哪些新闻推送给用户,事实上这是一种计算机智能编辑过程——而它的意见立场是不透明的。
以上这些技术变革的结果,是一些原本由传统记者完成的任务,以及所采用的方式,被颠覆了。记者可以在社交媒体或计算机程序Storyful上手工筛查爆炸性新闻或者热门故事。他们可以使用Grammarly这样的写作程序来进行新闻的编辑工作,还可以用印象笔记(Evernote)来做速记。这些新技术已经开始颠覆传统的记者工作内容了,但更先进的技术甚至开始取代记者这个职业了。2014年,美联社开始使用Automated Insights开发的算法,把原先需要人工操作的几百份业绩报表的整理过程变成了计算机程序,这一技术生成的报告数量是原来的十五倍。《福布斯》(Forbes)杂志如今也提供类似的业绩报告以及体育类报告,使用的计算机算法由Narrative Science提供。《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使用一种叫作Quakebot的算法,来监测美国地质调查所发出的地震警报,然后自动将相关事件生成为新闻……
2.5 管理咨询
2013年,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论“处在被颠覆的风口浪尖的咨询行业”,文中说,咨询行业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些以前帮助别人管理困境的人“即将被颠覆”。达夫·麦克唐纳(Duff McDonald)在他所写的《麦肯锡经验》(The Firm)里提出了他的观察结论,他认为咨询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提出过观点,“50年以后,类似麦肯锡这样的管理咨询公司将不复存在”。克里斯·麦肯纳(Christopher McKenna)把管理咨询行业称作“世界上最新的专业工作,他们是否确立了专业工作的地位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的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进一步解释他们的观点,克里斯坦森评论说,咨询业的商业模式在过去100年里没怎么变化过。一个聪明的局外人或者一组外部专家被派到组织内部花上一段时间,然后根据他们的观察和发现尝试提供(至少表面上)客户最关心的问题的“可能答案”。这些年,咨询公司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突出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声称他们的团队更加聪明、更为严谨,比竞争对手在特定行业拥有更多经验等。有些咨询公司还开发了专有的工具,让自己更为出众。安信达咨询公司和埃森哲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是其中的典范——他们开发的系统和管理的项目就像菜谱,延伸出许多不同的章节,一步步为人们展示如何完成复杂的流程。使用这样的方法,管理咨询行业似乎被精简成了一套标准程序。
过去,有些咨询公司还有一套绝活,那就是拥有别的公司所无法获得的数据和信息。储备充足的研究文库,人手充足的内部调研部门都是这种竞争优势的基础。几位与我们交谈过的战略咨询顾问估计说,以前他们公司可能花费了高达80%的时间来进行信息收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许多数据和信息都开始向公众免费开放了。如果这些数据还没有在网上公布,客户还可以借助传统的“调研机构”,比如说加特纳公司(Gartner Group)、弗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以及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来获取数据。数字化的流程意味着相比聘用顾问花时间手工统计人数、监控存货、处理各种数据表和数据库,客户将更加愿意自行收集基本的内部数据。客户数据可以通过直接收集“数据尾气”[6]来获得,或者来自于线下的创新活动,例如会员俱乐部信息(1650万人使用乐购的会员卡),或者收集其他未经整理的原始数据,而不是进行特定调查或者面对面的访谈。基于关于这些变化带来的思考,有一位咨询顾问告诉我们“他们业务模式的核心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对战略咨询公司来说,数据与信息收集工作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0%。
基本分析工具以及复杂系统的普及,也使得传统咨询业以外的人能够进行数据处理,得出以前只有咨询顾问才能发现的观点。曾经以1张图片表达深刻信息的咨询公司贝恩(Bain Capital),其单个项目的收费高达100万美元,而如今,咨询公司再想创造出“价值百万的幻灯片”已经不那么容易了。这一技术变革的结果是,传统的战略咨询公司把大量日常调研工作外包给海外机构。像贝恩和麦肯锡都拥有海外研究团队,大部分在印度,分别被称为贝恩能力中心(Bain Capability Center)和麦肯锡知识中心(Mckinsey Knowledge Center)。这些海外研究团队为公司的正统咨询顾问提供各种支持;信息技术咨询顾问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将许多的日常工作转移到了人工和运营成本更低的国家。埃森哲和凯捷三分之一的员工都在印度工作。
除了外包之外,大多数公司还在更加复杂的分析能力上进行了投资,尤其是大数据,力求重拾并维系他们在数据分析方面的优势。有些咨询公司已经把他们新开发的数据分析能力打包成一种全新的标准化产品了。客户可以从事先准备好的软件和工具里做出选择,不需要由咨询顾问为他们从头准备一套全新的方案。以麦肯锡为例,他们为客户提供了16种产品以供选择,叫作“麦肯锡方案”;德勤(Deloitte)则设计了9种各有特色的产品,叫作“德勤管理分析”。客户一旦安装了这些软件工具包,就可以得到一系列由计算机分析得出的深刻观点,它们取代了传统的幻灯片或者最终报告形式的一次性专业知识交付。
对于旧式的战略咨询机构来说,传统的战略工作变少了(一位资深业内人士把这类工作描述为“画曲线”)——如今只占他们工作比重的20%,而30年前这一类工作要占到他们整体业务量的60%~70%。许多咨询公司都被迫开始对某个特定区域或行业进行深入研究,只有那些最大的咨询公司还保留着全面战略通才,或者说“系统层面”的能力。在今天,信息技术咨询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但也同样面临着来自于低成本供应商的竞争。这里有一个定义上的问题——有些公司并不把系统开发的工作归类为“咨询业务”的组成部分,但对另一些公司来说,这就是他们所提供的咨询业务的核心。
在传播和宣传的渠道上,波士顿咨询公司、贝恩公司和麦肯锡咨询公司,这三家世界上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都组建了清晰的“思维领导力”业务板块,来传播他们从典型的咨询项目中所获取的经验。另外,一些新的咨询业务形式也已经出现,比如说波士顿咨询数字化创投公司(BCG Digital Ventures)和德勤数字化咨询(Deloitte Digital)都以提供的“数字化”咨询为主要服务内容;曾经隶属于英国政府、目前属于NESTA基金会的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提供的“行为”咨询。
在传统的咨询机构范畴以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咨询顾问、小型的精品咨询公司,以及专攻研究和数据分析的公司,他们都在积极地抢占市场。谷歌的首席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Hal Varian)把这些现象叫作“微型企业”(micro-national),称它们“借助互联网,拥有了15年前只有大型跨国公司才能负担得起的沟通成本”。互联网也为利用众多专家顾问所构成的网络来定制服务提供了便利。格理集团(GLG)和凯博公司(Guidepoint)让客户能够接触到他们庞大的在线专家资源,分别达到了40万和20万人的规模;商业类人才集团Eden McCallum和Cast Professionals则有能力动用经过审查的自由职业顾问资源,在线上和线下为客户组建更加正式的临时团队;10 EQS的团队只提供在线服务,客户和团队通过指定的在线平台进行互动;而Expert360、Skillbridge以及Vumero则更加像是一个在线集市,帮助客户按照他们的需求筛选个人顾问;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是一个会员制的在线咨询业务平台,其专家网络拥有16000名中高层管理人员,他们为客户寻找并传播最佳实践经验。
最近还出现了咨询服务的众包平台。Open IDEO是设计咨询公司IDEO所创立的在线平台。许多问题,大部分是社会问题,被公布到网上,任何人注册之后都可以登录到Open IDEO平台以协作的模式去贡献自己的想法;Wikistrat是一个在线网络,拥有大约1000名各种背景的专家,他们来自于政治、军事、政府以及学术领域,用户向一群选定的专家定向提问,这些专家就通过Wikistrat聚集在一起来解决相关的问题;Kaggle也是一个在线平台,客户提交自己的数据并提出相应的问题,来自于100多个国家的统计学家会相互竞争,尝试提出最为深刻的分析。这类众包服务不仅仅针对个人用户,甚至于英国政府的内阁办公室也有一支开放式政策制定团队,他们使用各种在线平台(博客、社交媒体、众包)来尝试打破公务员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垄断”传统。
也有些系统不需要太多来自人类的输入。Ayasdi和BeyondCore这样的平台专业提供“自动化”的数据分析——据说这些系统会自行通过挖掘数据中的相互关系,来寻找有趣的发现再用于下一步分析,或者指出还需要哪些额外的数据,不再仅仅只是等待人类提出问题。调整相关设定后,IBM的沃森计算机也可以扮演“企业高管顾问”的角色——它扫描各种战略文档,学习消化会议内容,并且针对不同问题根据它的观点提供分析性的建议——比如说,对于给出可供投资的公司的建议。Kensho是高盛投资的一个系统,可以用简明语言回答本来需要大量人工调研的金融问题(例如,如果发生隐私信息恐慌,技术类股票会如何表现等)。
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咨询公司的业务模式,也改变了客户的行为:传统咨询公司发现,客户对使用外部协助的态度越来越谨慎;当他们不得不使用外部协助时,他们更愿意将任务进行分解(把任务拆分成几个子项目);他们也更乐意使用不同的人和系统来避免对某一个供应商产生依赖。有一位顾问把这比喻为“皇帝的新装时刻”——客户突然意识到他们(咨询业)的所谓技巧,从“作业成本分析法”到“基于价值的管理”,并不如原来想象的那么复杂。
有些传统顾问认为,企业内部的自有顾问是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企业内部顾问团队的兴起部分得益于数据和网络分析工具的普及。另一部分是由于受雇于这些企业的自有顾问,多是从传统咨询公司离开的人员,他们也具备分析的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被视为经典的顾问合格证的MBA学位也变得更为普遍了。随着商学院逐步开放这些MBA课程,这一现象会进一步加速。从2014年开始,哈佛以前独有的、两年学费高达90,000美金的MBA课程,随着在线学习平台HBX的诞生得到了补充。这一课程提供能够更快完成在线认证CORe,其费用仅为1500美金(被描述为“商业基本原理的初级课程”),在九周内为学员们提供一系列的专业商业课程。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并不是毫无争议的——哈佛商学院两位最有名的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以及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就公开表示对这种做法的不认同态度。对于企业家和小业主来说,互联网可以支持他们发展更加“自助的”文化。在线下,美国每年出版11000本商业类书籍,还不包括个人出版的书籍。在线上,作家、从业者、学者,以及外行人士形成的网络,通过许多不同的平台和社区,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思考问题的知识框架已经标准化——比如说芭芭拉·明托(Barbara Minto)所创建的“金字塔原理”,它是各大咨询公司运用逻辑去分析解决问题的常用工具,这曾经是麦肯锡专属的工具,但现在这一工具的文字性说明、视频解说、在线课程,甚至应用程序“Minto”都已经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
缺乏正式的专业边界,让各咨询公司发展出了各自的特色,而不像其他专业工作领域内每家公司的业务都相对雷同。比如像埃森哲,如今聘用了750名医院护士,他们超过10%的收入如今来自于“数字营销”方面的建议,尽管这听起来更像是广告营销公司的业务。纵观当今世界咨询行业,随着新技术的普及,像埃森哲这样,传统的管理咨询服务所占的业务比重已经非常小的公司其实为数不少。
2.6 税务与审计
大部分税务和审计工作都是由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这两条业务线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是受到高度监管的,都需要定期和国家互动,工作的基础都是财务数据。尽管已经成为巨蟒剧团(Monty Python)著名的嘲讽对象,会计师还是在现代经济里扮演了非常核心的角色。然而,有迹象表明,他们所做的许多事情也正在面临技术的挑战。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人工智能领域所做的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就已经认定,人工智能技术在税务会计领域有许多可做之事,随后80年代的各种电子表格软件和微型计算机(这都是当时的名称)都受到了行业领先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推崇。
让我们先来分析税务工作。过去纳税人在填纳税申报单时,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完成这项任务,或者聘用一位熟悉相关法律和操作的人类专家,来分析他们的信息,代表他们完成这些表格。后者是一个非常诱人的选项。大多数地区的税务条款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变得非常繁复,甚至可以长达几千页,而且文字深奥晦涩,还经常变化。比如说,在美国,近年来税务条款平均每天更新一次,但是事实证明“人类专家”这个选项非常昂贵。历史上,每个客户的税务建议都是“人类专家”手工完成的,而且建议也是量身定制的。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税收计算甚至还需要通过对大量账目和纸质账单进行漫长的人工梳理来完成。
但是近年来,纳税人拥有了第三种选择——在线的辅助填写纳税单的计算机软件。个人使用这些应用程序时,只需要回答一系列简单的财务问题,软件就会自动为他们生成纳税申报单,过程中不需要任何人类专家。2014年,将近4800万美国人自己在网上完成了纳税申报单,没有使用税务专家的帮助,而是使用了税务软件。大多数软件供应商还提供相应的在线服务,纳税人和税务专家在这些平台上交流经验、分享所收到的各种建议和指导意见。
2015年3月,英国财政部长宣布了“纳税申报时代的终结”,并宣布于2016年启动“数字税务账户”。过去,个人和小型企业同样需要会计师来帮他们监控现金流、处理发票、记录费用以及其他,现在这种在线财会软件的数量与日俱增,帮助人们借助计算机来完成其中的许多任务。由于和英国税务机关有着合作关系,在线财会系统Kashflow甚至把整个增值税申报手续都电子化了,于是所有使用它们的系统来进行财务记录的公司,在年底都可以使用自带的程序自动生成完整的纳税申报表,然后通过网络迅速完成归档。而其他财会系统要具备同样的功能,其实只需要再往前跨一小步而已。
相比个人和小企业,大型机构需要处理的税务事务更加复杂,他们可以动用的税务技术就更多了。例如有些系统可以抓取税务申报所需要的数据、计算需要缴纳的税金、递交最终的税务申报表、编制正式的账单和报告、预测并测试不同的税务策略的效果,而这些都是自动完成的。有些税务系统甚至非常激进:英国的德勤公司,把大约250名税务专家的经验共同提炼整合到一个系统里,来帮助主要的客户准备并递交他们的企业纳税申报单。当2009年德勤把这个系统卖给国际信息提供方汤森路透集团时,“《金融时报》100指数”中70%以上的企业都已经在使用这个系统了。德勤另一个系统,用于申请境外支付时增值税的抵扣工作,也不再由人类专家处理,而是交给了Revatic Smart系统。它利用光学字符识别软件来扫描客户的文件,然后在非常少量的人工帮助下,自动将所有扫描结果提取为正确的格式。
在过去,国家税务机构和他们的运营,很多仍然依赖于纳税人,从个人到大型跨国企业来进行自我评估。标准流程是,人们登录到某个系统里,真实地回答一组问题,在指定时间按照规定的格式提交申报单。但现在,一些国家取消了大部分的自我评估工作。这些国家的企业不再需要准备纳税申报单。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直接把原始的财务记录以电子记录形式提交给税务机构。税务机构使用这个名为数字记账的公共系统(SPED),通过分析所提交的数据来决定需要缴纳税金的数目。这类计算机系统还可以用来解决避税和舞弊行为。比如说在拉丁美洲,一种流行的避税手段是使用假发票,通过记录虚假交易来减少应付税金。而现在,智利、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的税务局都制定了强制规定,要求企业在交易发生时及时向税务机关在线提交“电子发票”,用于取代传统的、容易造假的纸质发票。同样的,在意大利,税务机构使用“Redditometro”系统,搜索已有的数据,估算某一个特定的纳税人在某一年度可能的开支——如果估算结果比纳税人在申报单上所填的要高出20%以上,他们就会要求纳税人做出解释。在美国,有好几个州使用了律商联讯的Risk Solutions,这个系统使用了一套算法去梳理数据,来识别使用虚假身份申请非法退税的税务欺诈者。但是,此类系统所涉及的数据量是巨大的。英国税务机构使用的舞弊识别系统“Connect”,经常为了得出某一结果而筛选上亿条信息。据说这个系统拥有的数据量比大英图书馆还多,这做起来绝非易事,因为大英图书馆藏有每一本在英国出版过的书籍。
随着许多税务事务变得数字化,税务专业人士的日常工作也正在发生变化。巴西,就是取消纳税申报单的国家之一,该国的纳税机构收到的将是原始的账目(而不是纳税申报单)。这已经改变了巴西几大税务咨询公司的工作内容。他们不再帮助客户准备纳税申报单,转而帮助客户准备他们的原始账目。为此,他们使用的软件也转为了税务机构最终指定的报税软件。
对于更加传统的税务事务所,竞争则来自于不同方面。企业内部的税务团队、管理咨询顾问、软件开发团队以及商业信息提供方都对税务工作越来越感兴趣了。为了应对这些,传统的税务事务所对合规性工作(准备和递交申报表)的关注减少了,转而接手更多的税务规划工作(例如在哪里设置公司总部或者选取哪里设立永久实体来降低税负)和交易咨询工作(例如对并购项目的税务影响提供建议)等。这些建议都越来越具有前瞻性,而不是被动反应性的。比如说德勤,基于手机的GPS数据,对外籍雇员提供计算机建议,告诉他们可以或者不可以去哪个国家地区,来最小化他们的税负。
随着技术发展,税务专业也面临着特别的风险。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在《未来的雇佣关系》(The Future of Employment)一书中推测,在计算机时代,只有1%的税务工作者是安全的。在他们所审阅的700种职业之中,税务工作被认为是十大“风险最高”的职业之一。目前全球每年有61亿小时被用于税务申报工作,相当于300万个全职工作岗位,因此发生的变化将非常巨大。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里所提到的奇异现象,通常可以让从事规划和交易咨询的税务专业人士迅速承认,与自己工作内容是有差别的、从事税务合规工作的同事们的工作已经受到了无法回避的威胁。然而,这些规划师和咨询顾问自己的工作也已经危在旦夕。早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已经认识到,税务规划和税务合规工作,从技术上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都在同样复杂的规章制度框架内运作。两者之间的唯一差别在于,从信息处理的角度来说,税务合规工作按照法律和事实的框架来对信息是否符合规则进行判断,税务规划工作也需要在法律和事实所界定的框架内,但他们更多的是进行理性思考,如何使目标税负符合规则。这种根本上的相似性得到了世界上税务工作领域的思想领袖的呼应,他们认为许多税务规划工作很快将同样由机器来完成。对于那些为并购交易提供建议的顾问,领先的会计师事务所正在寻找(追求进步的企业内部律师也是如此)可以完成尽职调查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也在努力标准化大多数文件归档。税务工作的转型正在逐步进行中。
行业领先的审计师也同意他们已经身处根本性变革的边缘,但据他们观察,审计行业的转型没有税务行业那么快发生。这通常都是由于立法者的保守态度,他们总是被认为十分抗拒新的工作方式。审计是门大生意。全球市场领先者普华永道,为全世界30%的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雇用了大约70,000名全职员工,分布在157个国家和地区,所提供的服务总价值超过100亿美金。而世界上大企业的审计工作基本被包含普华永道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所主导(其他三家是德勤、毕马威和安永)。2013年在英国,“《金融时报》100指数企业”中98%、“《金融时报》250指数企业”中96%、所有企业中的78.8%都是由“四大”提供的审计服务。然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从没有一家想过要去采用彻底不同的方法来打破这个市场,也许原因在于这些事务所的在位者缺乏明显的动力去改变现状。
审计师在商业世界里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就像税务专业人士一样,他们的工作是基于财务信息的。但是他们的工作也非常不同,对合规工作而言,税务专家通常为企业管理层服务,他们审阅财务报表,计算并且尽可能减少应交税金。与此相反,法定审计师被请来审阅财务报表,以保证其准确性、完整性并且确保财务报表合理反映公司的实际业务活动。简单说来,审计师确认或否定公司所公布的财报的真实性。审计工作的最终用户是投资者,他们的投资决策将受到审计师意见的影响。因此审计师可以提升投资者对于某些公司或者更广泛来说,是整个市场的信心。
尽管审计师的工作如此重要,财务审计中有许多流程驱动的工作这一事实是很清楚的。数十年来,标准的检查清单为这些工作提供着支持,而大型事务所则开发出了更为复杂的审计体系,就像毕马威的KAM和安永的GAM。这些体系为如何开展基本的审计工作提供了手把手的指导——从计划、风险评估、控制评估、测试交易和账目,到最终的财务审计报表。财务报表审计对技术的依赖性是早就存在的,20世纪80年代审计师是电子表格和微型计算机技术的最早期使用者,行业内也曾经有过大量关于“审计自动化”相关可能性的探讨。也是在那个时代,计算机审计开始出现——除了审阅纸质材料以外,审计师必须学会审阅、查询计算机会计系统。从那时起,“计算机辅助审计程序”(CAAT)经历了几波发展。如今最大的事务所都已经开发并且用上了他们自有的软件——比如普华永道的Aura系统。这些系统被设计来执行复杂的大型跨国公司的审计。它们协助标准化审计流程、抓取分析相关数据、协助进行项目管理,并对审计过程进行记录。
在不那么复杂的审计中,众包的形式得到了推广和使用。比如2009年英国政府在网上发布了70万份英国议员工作时所产生费用的文件。作为回应,《卫报》为这些文件搭建了一个在线平台,对任何个人来说这工作量都过于巨大,所以《卫报》要求读者们一起对这些文件进行筛查,并且将可疑的地方揭示出来,如果有项目需要分析,则可以自由添加文字。超过2万人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事实上,这就是一次公共审计。
企业审计工作则有着明显的复杂性,但我们也经常听到强烈的改革呼声。一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垄断地位表示担心,以及他们所从事的非审计业务;另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人们过去对审计师表现的失望情绪所引发的改革期望。观察人士和怀疑论者希望了解,就像约翰·C.科菲(John C. Coffee, Jr.)在他的书《看门人机制:市场中介与公司治理》(Gatekeeper:The Profession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里所说的,为什么“看门狗没有发出警告”——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安然和世通公司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对他们的财务丑闻发出警告。
改革的另一个驱动因素在于,领先的审计师也坦白承认,目前的计算机辅助审计程序还不足以处理如今的大型审计项目所涉及的庞杂信息和交易数据。理想世界中,审计师应当能够审查一个企业每个年度里的每一笔交易记录,并且核对它们是否已经如实反映在账目中。实际上这并不现实。大型审计项目中,有太多交易需要审核。无论是单纯通过手工审计,还是使用计算机辅助审计程序,数据量都过于庞大了。相应的,复杂的技术被开发出来,审计师事实上只需要检查一小部分经过仔细筛选的交易。这一小部分被选中的数据叫作“样本”。在选择样本时,审计师被“重要性”水平所引导(浅显说来,如果达到重要性水平的财务信息发生错误或者遗漏,可能影响投资者的决策)。作为传统惯例之一,他们依赖“试探法”,用简单的经验法则来帮助他们发现账务处理过程中通常的错误和典型的遗漏。通过检查小规模的样本和试探法,审计师得以对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做出更宽泛的结论。他们也曾尝试将其他工作补充到这些分析工作中来——在客户的场地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在客户办公楼面上走一走——以对正在审查的业务获取一些真实感受。但最终,审计师必须承认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固有缺陷——从有限的样本量中做出推断是有风险的(即便统计学上也是站得住脚的),他们的“试探法”也通常具有误导性。但审计师采用这样的方法也是不得已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审计师必须处理的数据量正在高速增长——一个客户一年的数据可能达到几十亿条,甚至上万亿条(最大的客户每周的交易数量都往十亿的数量级发展了)。因为这些被审计公司的业务规模日渐庞大,还因为企业开始系统的以数字形式记录并保留所有业务活动。传统的方法,按照我们上面所提过的,是取一小部分样本并将结论推而广之。
审计行业的新系统应该能够处理更大的样本量。有些情况下——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变化——他们正在试图处理所有的数据,完全抛弃取样抽查的方式。这正是普华永道正在开发并推广使用的审计软件HALO的理念。它的设计使它能够通过计算机算法处理所有的数据(也就是所有的交易数据),然后找出其中的异常和矛盾之处。这也符合毕马威的詹姆斯·P.里迪(James P. Liddy)所做的预测,未来的审计应当具备“对客户所有的交易进行检查的能力”。
“百分百测试”的雄心壮志——使用所有可供调用的数据,不仅仅只使用一组具备代表性的样本——正是在统计领域普遍流行的想法的特定体现之一,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I nberger)以及肯尼思·库克耶(Kenneth Cukier)在他们合著的《大数据时代》(Big Data)一书中谈到过。大数据时代的一个总体特征,在于从选取少量样本转变到使用所有的数据(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从部分到全体”)。“百分百测试”的下一阶段是一种被前沿审计师称为“连续审计”的现象。利用可以获取更多不同来源数据的平台,将持续性的交易审核和传统的财务报表审核进行结合,目的在于能够实时了解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这再次反映了大数据时代的总体优势——结合使用不同来源的数据,格式各不相同,结构也不那么正式(但不包括电子表格里仔细整理过的数据)。总而言之,未来的审计将使审计师大量使用“各种凌乱”的数据,这意味着他们能够通过将一个企业和其他对照公司“各种凌乱”的数据集进行比较,能够深入了解这一企业的财务状况。与这种方法类似的有“十亿美金价格项目”(Billion Dollars Prices Project),它是一种新颖的美国通货膨胀的计算方式。当下的做法是,由美国劳工统计局派一小队调查员,针对那些经过仔细筛选的样本企业,以标准格式记录下某段给定时间内一些具体产品的价格变化,并且定期发布调查结果。这十分类似于经典审计工作中的“选取样本并且得出推论”的做法。这种传统方式目前每年需要花费2.5亿美金。爱德华多·卡瓦略(Eduardo Cavallo)和罗伯托·里哥本(Roberto Rigobon)两位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们负责的“十亿美金价格项目”另辟蹊径,使用软件来搜索网络,每天收集分析50万条不同格式、不同地区的价格信息,来更为频繁地获取通货膨胀信息,而这一做法的成本低得多。这种更宽泛意义上的审计(测试所有的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可以和许多会计师经常引用的“鉴证”概念更好地匹配起来。当人们对业务和投资做出决策时,他们通常寻求财务审计范畴以外的相关因素的鉴证(比如说,特定行业的某些行业业务数据)。领先的会计师事务所如今都在对他们的业务范围进行拓展,将鉴证(以及风险管理)服务包括在内。他们的优势在于这些鉴证工作是由值得信任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从而使客户充满信心。
对于审计和税务,专家预测所有的财务数据今后将以某种全球统一的标准格式(“XBRL”目前是风头强劲的“候选人”)得到呈现,相关工作都将使用更加强大的计算机算法、搜索引擎、代理、日常数据处理。也许传统的审计师会认为这永远无法替代审计师的“判断”(比方说,客户是否恰当地提取了各项准备),但领先的事务所已经在十分严肃地研究人工智能如何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了。
2.7 建筑
在过去,建筑被视为是一种“绅士”们的消遣活动。直到今天,它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名声。建筑师的培训内容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没发生过什么变化,但相关课程需要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让大部分人望而却步。在英国,从开始学习建筑一直到获得建筑业从业资格平均要花九年半时间。对个人来说,获取资格需要花费的成本比任何其他专业工作都高昂——毕业的时候,建筑类学生的贷款一般达到10万英镑左右,相比之下,法律毕业生贷款5万、医学毕业生贷款7万。如此辛勤耕耘的成果却并没有开花结果——在美国,建筑设计中直接用到建筑师的比例只有区区5%。菲利普·约翰逊(Phillip Johnson),这位杰出的美国建筑师曾经戏称:“从事建筑行业的首要规则是你得含着金钥匙出生,如果这一点不成立,那么第二条规则就是嫁个有钱人。”
几十年前,每当建筑师接手一个新项目,他们用一张白纸、一套手工工具(圆规、丁字尺、铅笔等),为客户起草设计图纸和工作计划。“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的出现改变了这些程序。桌面设计软件诸如AutoCAD、Revit和CATIA取代了那些传统的工具,数字设计也代替了手工绘制的设计。它们的出现导致了大卫·罗斯·舍尔(David Ross Scheer)所说的“绘图时代的终结”。事实上,尽管使用了数字化手段,但大量的建筑工作仍然在走定制化路线——比方说,建筑师手工把创建的各个设计元素点击、拖拽、放置到屏幕上的某个位置。如果这样来操作的话,CAD仅仅是简化了原来的方法。但是数字设计相比手工设计,细节可以更加完善,修正更加简单,设计方案也更易于分享以及再次使用。新技术还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可以用三维模拟来进行演示、探讨方案、分解方案、重新组合、颠倒上下、放大缩小,并且可以采用不同的形状和结构来进行无数实验。所以,比起以前,这些系统为制图员们创造了更多可能性,提供了高度灵活性。当项目变得数字化、更加易于分享之后,建筑项目也变得更容易利用各种不同背景的专业人才——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机械顾问、电力顾问、设计师、承包商、供应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工作模式,收集自己所需要的数据,关注建筑的不同方面。这改变了以前建筑师掌管项目,统筹每项任务的局面。为了协调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新的在线平台“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已经被开发出来了。人们不再需要依赖手工绘图或者CAD草图,这些在线的BIM平台可以把各路人士在同一个项目上互不相干的工作成果整合到一起,组合成一个巨大的、共享的虚拟模型。这样一来,外包某项特定任务就变得非常简单,据说这一数据相当于印度平均每天成立一个新的工程学院。
CAD系统还有许多更复杂的使用方式,它们一并被称为“计算机设计”。这些方法负责设计各种曲线和圆顶——“流体建筑”——在当代建筑里比较常见,比如说,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或者伦敦的市政厅(“蛋”)。其中有一个相关领域,叫作“参数化设计”,建筑师们不再手工绘制某一幢建筑物,而是通过一系列可调节的“参数”或变量,使用CAD来创建一组建筑群。当这些参数被进行调整时,这个模型自动为每幢建筑物生成一个新的设计版本。更为激进的是“算法设计”——建筑师设定好某个建筑的设计要求(比方说,结构强度或者环境绩效),由计算机算法从各种可能的参数值里进行仔细筛查,设计出最符合要求的方案。Autodesk是一家提供CAD软件的公司,他们正在试图通过所谓的“追梦项目”更进一步——它是一个可以通过一组设计要求,自动生成许多可能的数字设计方案的软件(目前,Autodesk已经用这个软件设计出稳定的椅子和轻量化的自行车框架了)。
同样的,“计算机辅助工程分析”面世之后也改变了结构工程师的工作。曾经需要制作用于结构测试的实物原型被计算机模拟计算所替代,其测试要求也远比以前严格和精准。计算机性能的进步意味着更加复杂、对计算要求更加苛刻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处理,因此为人类创造了去尝试更加高风险的建筑项目的条件。目前,最杰出的结构工程师正在向相关行业取经,比方,通过向航空领域学习,使用计算机技术来解决结构工程的问题(结构工程师从航空学中学习飞机周围空气流动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理解空气在建筑周围流动的方式)。
对非专业人士,也有更为简单,但仍然不失实用性的CAD系统。大多数都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通常还是免费的,像SketchUp、Chief Architect还有MatterMachine。这些系统让人们可以搭建虚拟模型,自行完成从小型的产品甚至到整个家的设计,并将之变成正式的计划。另外还有可以解决非常特定设计问题的其他CAD系统,例如Ply Gem的Designed Exterior是一个免费的平台,它帮助用户完成房屋的外部设计(窗户、护墙板、排水系统等);TimberTech的Deck Designer 是另一个免费平台,帮助人们设计户外地板,还有许多仅针对厨房、浴室、书架设计等的设计平台。把这些系统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很有可能像斯蒂芬·库鲁兹(Steven Kurutz)在《纽约时报》里写的那样,“完全跳过建筑师”。
还有一些在线平台也在从客户关系的角度,对传统的建筑师发出挑战。在WeBuildHomes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网站所提供的一些固定的“结构单元”来设计一个虚拟的家,然后在网上递交自己的方案。人们可以浏览网站上的各种最终设计,从中寻找符合自己预算和品位的方案,如果找到合适的方案,WeBuildHomes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建造服务。在Arcbazar网站上,人们可以提出设计需求(从简单的装修到大规模的建造),设置一个截止日期以及相应的报酬,任何认为自己能够胜任的人都可以递交自己的方案和其他方案相互竞争并最终赢得报酬(平均每个项目有9个人递交方案)。WikiHouse是一个开放式的设计师社区,他们在线上协作设计房屋,设计方案可以被打印出来,没经受过培训的人也可以根据这个方案完成组装,房屋的总造价不超过50,000英镑(2014年9月在伦敦由8个志愿者花了8天时间组装了一个早期的WikiHouse版本)。在Paperhouses网站上,建筑设计公司把他们的设计蓝图以开源形式放在网上,供大家下载并使用。人们还可以在Open Architecture Network上发布相关的问题,由在线社区里47000多名设计师一起来解决。
互联网服务不仅仅可以为项目寻找灵感,也可以为项目筹集资金。比如说Prodigy Network使用他们的在线平台为位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一幢66层楼的大厦BD Bacatá(该国最高的建筑)进行众筹,从4200人手里筹集了超过2亿美金。也有规模小一点的项目,荷兰鹿特丹为一座39米长的木桥Luchtsingel筹集部分资金,用户为某根木板或某个部件承担费用。在伦敦搭建的WikiHouse的项目也是用这种方式来筹资的。
现在许多用于修建建筑的机器和工具也都开始计算机化了,不用再进行手工操作。这些机器和工具都接受着能够进行数字设计的计算机系统的指挥——被称为“数字制造”或者“计算机数控”(CNC)。传统上,用于建筑类的机器执行的是“消减制造”的方法——最终产品是从一个更大的物件上削磨出来的,或者从一大片材料上裁剪而来。在人们广泛谈论3D打印技术的今天,人们开始逐步采用增材制造的思路——他们逐层打印薄薄的材料,层层覆盖,逐渐搭建出最终的物品(因此,3D打印的别名叫作“增材制造”)。它们的重要性功能在于能够制造更加复杂的物品,或者按照需要制造小批量的物品(有时候被人们叫作“大规模定制”)。3D打印机一开始被用于制造小型模型以及将初步概念“快速制成原型”,但现在,它开始被用于制造和构建最终的建筑物本身。2014年初,荷兰建筑事务所DUS Architects,组装了一幢完全由打印部件建成的房子,用来打印的机器可以打出高3.5米的物体。几周后,来自中国的某建筑科技公司宣布在一天之内,他们打印了十幢房子,使用的机器长32米、宽10米、高7米。2014年底,NASA把一台3D打印机送到国际空间站,测试它是否能够按照需求打印出工具和零部件(甚至食物)。
随着这些工具的成本下降,它们开始出现在一些非常规的情形。比如说来自于明尼苏达州的工程师安德烈·卢金科(Andrey Rudenko),自己组装了一台水泥打印机,在他家后院里设计并打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城堡。越来越多的社区工作室都配备了这些工具,成了所谓的“创客空间”或者“微观装配实验室”。引用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创客:新工业革命》(Maker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里写的话,“我们如今都成了设计师”。
在这些新兴技术的影响之下,设计活动和建造活动之间的边界似乎已经变得模糊。机器人装备上了“几乎所有人类想象得到的工具”,然后被用于装配建筑。其中许多都是在其他工业环境里看得到的“机器臂”(以前的正式名称是“六轴”机器人,因为它们有着六根单独的轴或“关节”)。有些机器臂被用于处理材料,钻孔、切割或者铣削。比如说英国的“种子圣殿”,成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热门场馆,同时也是那年英国接待游客最多的景点(击败了传统常胜将军大英博物馆),不动用机器人的话就无法把它搭建起来。建筑物宽15米、高10米,周身插满6万根、每根长达7.5米的亚克力杆,每一根亚克力杆都需要插入一个尺寸精确的钻孔,最终完成的建筑物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发光刺猬。还有一些机器人负责运输物料以及组装工作,比方说,ROB Technologies公司的BrickDesign软件根据数字设计方案使用机器臂来堆砌砖块,它们能够实现的图案和形状让最熟练的人类都难以复制出同样的效果。传统建筑通过手工制作混凝土浇筑使用的模具来得到砖块,这一制造环节构成了混凝土建筑成本的60%。现在,Gramazio & Kohler公司的Mesh-Mould使用一个机器臂,前端装有一个小的3D打印喷头,可以在建设过程中直接“打印”混凝土砖块。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机器人能够完成涂油漆、浇注、打磨、焊接等工作。在更加激进的情形下,单个机器人被一大群机器人所取代。2012年,Gramazio & Kohler 使用了一组能够自动飞行的机器人,用1500块砖搭建了一个结构,在另一个测试里,这组机器人在空中用绳子编织和打结(叫作“飞行装配建筑”或“集体建造”)。2014年,哈佛大学的工程师建造了由1000个机器人组成的群体,它们不需要人为干预,能够通过自行组织,组成一些复杂的二维构造(类似于一群鱼或者一队蚂蚁)。另一种新方法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教授内里·奥克斯曼(Neri Oxman)开发的一种“群印刷”的方法——一组独立自主的机器人,每个都配备一个3D打印喷头,它们分头飞着完成打印任务。
在制造技术的革新之外,大量在线社区可以为其中大多数系统和工具提供辅助支持。比方说,那些使用基础CAD软件的人就可以利用大型的线上数字图书馆,人们在此存储和分享各自的设计——其中包括the SketchUp 3D Warehouse,收录了数百万个设计,还有GrabCAD,保存了超过66万份设计供人们借阅和重复使用。对于那些更为复杂的软件的用户,也有针对Grasshopper软件(和CAD软件类似)的社区,开发人员在社区里分享代码,互相帮忙解决错误、排查故障;还有Archinect这样更加正式的在线社区,建筑师和工程师在这里分享彼此的经验。不那么正式的可搜索档案馆Architizer,以及对所有人开放的虚拟剪贴簿Pinterest,借助它们,人们可以分享或搜寻最喜欢的设计和风格。各种各样的建筑博客也在蓬勃发展,比如说ArchDaily,目前,这一博客每个月的独立访问用户数已经达到了260万。
在建筑领域,像所有其他专业工作一样,我们都清楚看到了由技术引领的巨大变化的早期征兆。当加拿大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说:“未来已经来到,只是还没有均匀分布而已。”这句话也许就是他说给专业工作中的技术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