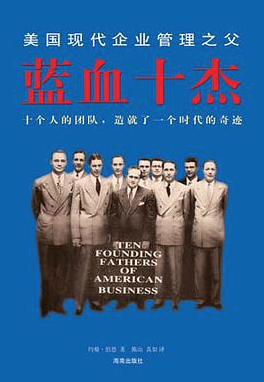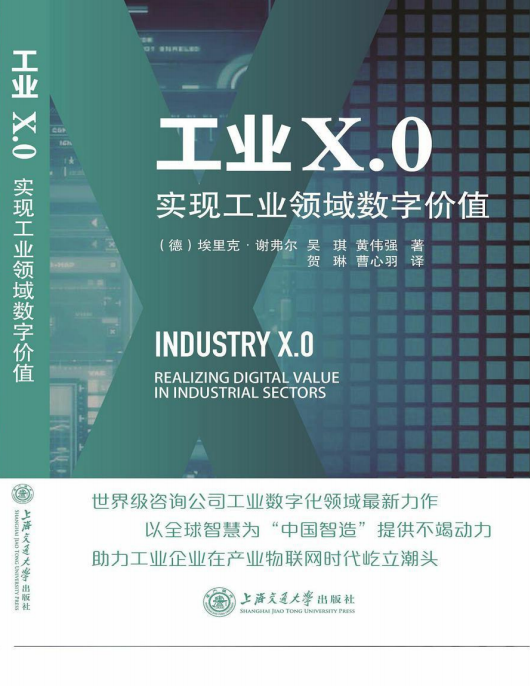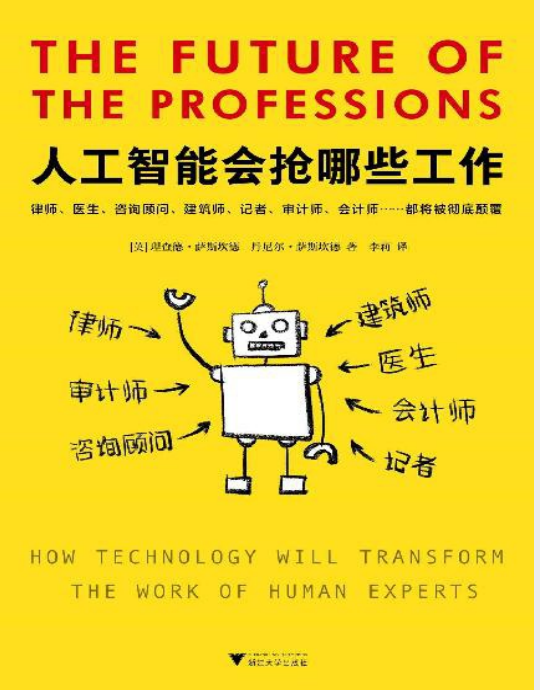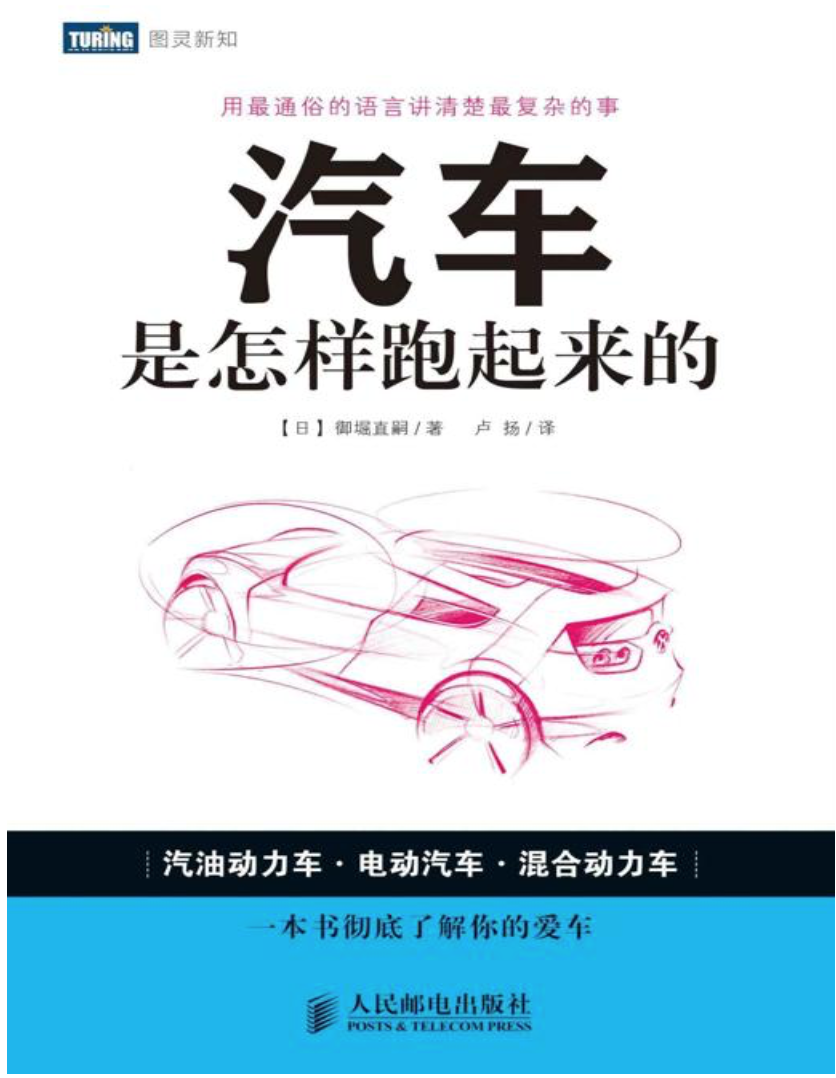20 闺怨
控制社会科技的这群人是世界的新教士,他们的宗教是企业的成功,他们的道德考验就是成长与利润。
——约翰·肯尼斯·盖布瑞斯
“这些人都是修道士,只是把祷告的经文换成了生产线,”一位传教士对《财星》杂志的记者这样表示。“看他们工作的态度,我有时会觉得他们是要用汽车把上帝淹没。我这么说也许很奇怪,但是我自己对教会都不像他们很多人对通用汽车、福特和其他那些公司那样的牺牲奉献。”
五十年代底特律迅速爬升的主管,个个都是为工作做牛做马、牺牲奉献。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是超人,福特公司更强化他们这个观念,公司给他们丰厚的待遇、认股权、气派豪华的办公室、免费的新车,而且让他们管理几千名员工。他们的家庭几乎成了公司的附属品,随时要待命参加福特的社交活动,还要全力支持有工作狂的丈夫。
鞠躬尽瘁
连他们应该住在什么地方,也要听公司的意见,绝大部分都是在布隆山庄的都铎式豪邸、法国式别墅或是殖民时期风格的庄园。这个高级住宅区距离市区有三四十公里,其间经过纷代尔、柏克利、洛伊橡园和伯明罕几个中层主管聚集的社区。从市中心一路到布隆菲山庄,其实就是一步步爬上社会地位的阶梯,每一个“等候区”就代表一个汽车人目前的地位,等到搬进布隆菲山庄,就是大家公认的功成名就了,就像利斯、莱特和米尔斯他们,现在都住在这个圈子。
一九六一年《财星》杂志下了一个结论,认为美国的汽车主管可能是全世界工作最卖力的经理人,不过大部分身受其害的主管家庭早就有这样的体认了。布隆菲山庄的一个医生说:“叫他们放慢脚步,简直就像告诉一只狗看到消防栓不可以抬起腿来一样。他们为新车出厂的最后期限赶工的时候,新车就成了上帝,这些人再也不是正常人了,他们只为那个期限而活。”
对他们的妻儿子女来说,最后的期限似乎一个又一个,永远也赶不完。非人的长时间工作、几百万几百万美元的成本、对家人无可衡量的疏忽冷落,为的往往却只是很少有人会多加注意的一些细节。有一次玛克辛的父亲到家里来玩,利斯很晚才回来,见到他岳父他解释说,为了“巡弋”的启动开关该放在哪里,他们讨论了一整天。他岳父笑他说:“我可以帮你省下很多时间和金钱,放在右边就对了。”还有一次,利斯说他的手下花了四天的时间,设法把行李箱垫子的成本减少三毛钱。玛克辛的爸爸觉得不可思议,最后利斯才解释说,三毛钱乘上一百万辆车子就是一笔可观的大数目了。
这些不胜繁琐的小细节,使底特律变成一个汽车城,心脏病发作的比例也居高不下。一九五三年的《商业周刊》有一篇报导说:“据说很多葬礼都排在接近中午的时间,这样亲戚朋友参加完葬礼之后可以顺便去吃午饭,而不需要离开办公室两次。
在这个地方,男人还在努力遵守着一些老旧的格言,例如‘困难的事我们立刻做到,不可能的事只需要多一点的时间’。”
他们在权力的金字塔上爬得愈高,距离平凡家庭的平凡生活就愈远,有些人满脑子只有汽车业的琐碎细节,连真实生活的喜怒哀乐都麻木了。结婚十年之后,利斯和玛克辛只剩下两个共同的话题:他们的孩子和福特汽车公司。在其他方面,他们几乎形同陌路,玛克辛无法理解利斯对工作的狂热,也无法理解他对家人的疏忽。
利斯告诉她,“你得要白天出门,把你想办的事情都办好,因为晚上我太累了,哪里都不想去。如果你不想做饭,那我每天吃玉米片也没有关系。你自己找人帮忙,白天出去把你想做的事都做好,可是我要待在家里。”
利斯的同事都相信,他对工作的关心远超过他的家庭,如果要他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做一个选择,他可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迟疑。公司的经理餐厅每天晚上都供应晚餐,而利斯部门的人出现在餐厅里的机会,高得不成比例。蓝迪的一个财务助理福瑞德·赛克瑞斯特回忆说:“晚上八点钟你还会碰到利斯,这是他标准的生活作息,不是例外。”
有的时候,玛克辛坦白表示她很羡慕米尔斯的太太海伦,因为米尔斯不知道怎么样,总是把工作时间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玛克辛问过利斯,“你和米尔斯都做同样的工作,为什么他能六点半下班回家呢?”
米尔斯不像利斯那样,为了往上爬几乎是不计一切代价。他不但乐于把职责授权给部属,同时也非常重视属下能充分发挥所长。他很少在晚上或周末加班,只有碰到关键性的期限或是真正的危机,他才会把工作带回家里;该休的假他也都会休,而且坚持部属要跟他一样。他大幅削减加班费,要求员工在上班时间内把事情做完,他说:“工作整天整夜之后,效率不可能不受影响的。时间花得多没有用,重要的是要看你的脑子有没有效率。如果超过疲劳的限度,你以为你还在工作,可是你其实只会把事情愈搞愈乱,因为你已经头脑不清了。”
活寡人
在一片制造汽车的狂热当中,很多人都头脑不清——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方面,有很多时间,利斯其实可以跟玛克辛分享他的想法和心情,但是他却把话都留在自己内心里。有一天,玛克辛的母亲从俄克拉荷马州打电话来,说要找利斯。玛克辛的父母都退休了,她心里一阵着急,她觉得她爸爸或妈妈一定出了什么事了。
玛克辛问她:“怎么回事?”
她妈妈一再说:“没事,我只是想跟利斯讲句话。”
“可是他现在不在,你吓死我了,一定有什么事情。”
玛克辛她母亲问她:“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今天他派人送了一部新车给我当礼物,他都没告诉你吗?”
“没有,妈,他没告诉我。”
“哦,这边的经销商通知我们说我们有一部新车,叫我们去领回来。”
玛克辛这才想起,两三天前她无意间提到她母亲那部破旧的老爷车,到现在还在开。他们并没有多谈,但是利斯显然记住了这件事,还想到送他岳母一部新的水星。偶尔他就会做出这样体贴的事情,使得玛克辛更没办法责备他疏忽了家人。后来她问利斯决定送车怎么没告诉她一声,他的回答只是:“哦,我想让他们惊喜一下,而且老实说,我根本没想到要告诉你。”
随着这些人达到更大的成就、更高的地位,太太的角色也愈来愈吃重。她们必须给她们的主管丈夫更大的支持,而一个称职的企业夫人,也要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诚如《组织人》的作者威廉·怀特在书中所说,对于五十年代训练有素的好太太,这些规范应该变成第二天性。
●勿与闺中密友飞短流长,尤其是丈夫在同一部门上班的人。
●不可邀请上司,应由上司采取主动。
●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可出现在办公室。
●对于你丈夫在升迁之路上可能超越的同事,勿与他们的妻子太过亲
密。
●对公司的任何人都不可留下不好的印象,也许有一天..
●要懂得妆扮,主管的成功与妻子的容貌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要经常与你丈夫的秘书通通电话、聊聊天。
●切勿——谨记,谨记——切勿在公司聚会中喝醉。这可能会留下不良纪录。
在社交场合上,有些福特太太们在拍照以前,一定要把手上的烟熄掉,桌上的鸡尾酒也一定要藏到椅子后面去,不愿意这些东西出现在镜头上。新车发表会、商展中的汽车促销活动、经销商的聚会,都有数不尽的社交义务,欢迎茶会、鸡尾酒会、午宴、盛大的晚宴,使这些组织人的贤内助应接不暇。
很多时候,这些部门主管跟经销商谈着正事,他们的妻子就得负责招待其他的夫人小姐,带她们去看服装表演、吃午饭、逛逛街。有时候利斯会打电话给玛克辛说:“我今天晚上需要一个太太。”这就代表又一次的生意上的应酬,每个人都在聊车子、公司和竞争,聚会中会碰面的客人,利斯会先把照片带回家,玛克辛就得坐下来把每个人的面孔和姓名背起来。这方面米尔斯完全仰仗海伦的好记性,她很容易就能把每个人跟名字对起来,在社交场合上轻声提醒她丈夫那些经销商和生意上的朋友姓甚名谁,为米尔斯避免了很多尴尬的场面。
对有些太太来说,这些送往迎来带给她们焦虑,不下于她们的主管丈夫在委员会上做报告的紧张。企业夫人最害怕的是做了什么可能令她丈夫没面子的事情,影响了他的升官机会。在迈阿密的水星新车发表会上,玛克辛一袭灰色的蓬裙礼服,裙摆上还饰有马鬃,她走过鸡尾酒长桌的时候,不小心碰翻了四杯酒,有两杯刚好洒在克罗素身上,虽然克罗素笑说没关系,玛克辛却是吓得说不出话来。
避开底特律的舞台中心,躲到安阿伯市去住的玛姬·麦克纳马拉,大概是最离经叛道的福特夫人了。她不像许许多多的企业夫人一样打打高尔夫,或是参加一些没什么匡正社会意义的妇女组织和俱乐部。汽车人太太每星期都会光顾的布隆菲中心十四球道的保龄球馆,她也从不去露面。其他的贵妇人都定期在这里聚会,个个争奇斗艳,比发型、比名牌服饰,顺便打打球、喝杯可乐,有说有笑。其他福特夫人对来访的太太小姐,总是招待她们看服装表演,玛姬却是带客人到密执根大学去看物理系上的回旋加速器,一种使原子核分裂的大型装置。她还加入底特律的联合国组织以及“妇女选民联盟”,对三个孩子玛格丽特、凯瑟琳和克瑞格更是宠爱有加,在一个几乎没有家庭存在的地方,建立起她的家庭。
麦克纳马拉在许多方面,也是跟他的子女形同陌路。他总是早出晚归,开车到迪波恩有一段路,往往天还没大亮他就出门,下班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克瑞格告诉一位访问者说:“我父亲从来没有跟我们分享过他真正的生活。”
米勒的太太法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是她所参加的唯一一个团体“安阿伯周一俱乐部”。周一俱乐部约有二十名家庭主妇参加,每星期一轮流在各人家里聚会,聊一聊佣人的问题、丈夫的问题,或是打打桥牌。除此之外,法兰的生活几乎完全都是绕着米勒和肯尼斯、小安这两个孩子打转。米勒难得有几个晚上不从公事包里拿出公文来看的,他女儿小安把这个无所不在的手提箱叫做“爸爸的皮包”。米勒说:“做太太的被忽略了,孩子也被忽略了,这是真的。但是她很体谅,对我非常支持,我太太一直没有回去工作,我不希望她上班。”
他们这群人的婚姻,在许多方面都像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家庭关系,家庭的幸福美满,不管是在感情上、心理上和日常生活,几乎完全都是太太的责任。玛克辛说:“上班时间你不能打电话找你先生,告诉他说水管不通了,你得自己找人来把它修好。”企业夫人有责任竭尽所能维持夫妻两人世界的美满和谐,她们完全是为丈夫而活,在这个游戏规则下,她们自己的兴趣、喜好往往都是次要的。
她们所过的日子,是充实的生活或只是丈夫的影子?有绝大部分,太太们也难脱关系。弗洛拉在大战期间嫁给了桑顿,但是当时她对他其实并不了解。她说:“不管是好是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我不能维持婚姻的幸福,我会觉得是我的失败。我还记得,以前我担心过自己的丈夫会被别的女人勾引,我就告诉自己:‘这种问题我可以应付得了。’结果桑顿是一个从一而终的男人,但是他的情妇就是他的工作,这样一个对手比起另外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更难对付。”
弗洛拉也跟玛克辛一样,很希望能够在她丈夫的事业上多参与一点点。但是,不管是哪个工作都全力以赴的桑顿,却从不让她分担工作上的成败。他说他一个人承受工作的压力就够了,他不希望弗洛拉也为他工作上的琐碎枝节而烦心,但是她宁可多了解一些细节,这样她反而会好过一点,因为她也会感受到他的压力。她说:“如果他有压力,我也会有压力,可是他以为他是在保护我,或者说他当时的确是做如此想法。”
安德森夫妻两个一起去上过“倾听的艺术”这门课,研讨会的老师曾经警告做妻子的,她们的主管丈夫给家人的时间会少得可怜,另外老师也教导做丈夫的要对妻子的生活适度表现出他们的关心和兴趣。
受到这个课程的启发,安德森家里养成一个有趣的习惯,他一回到家就会倒两杯饮料,跟珍两个人坐下来单独聊一会,谈谈他们白天的情形。珍说:“我们都觉得这样非常好,他到家以前我会把晚饭准备好,莎莉多半是在写功课或是在玩。如果我还在厨房里,他就会到厨房来,我们就坐下来,边喝饮料边聊天。我觉得很好,因为他会告诉我他在忙些什么。而且他也说,这样做对他也有帮助,因为他把我当做他的回音板。他说:‘我开始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你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很清楚应该怎么做了。’”
在安德森加入贝金斯公司一年多以后,有一天他回家告诉珍一个消息,说公司准备升他当审计主任,不过要等他有所表现以后才会给他正式的头衔和薪水。他说:“我得把公司的会计系统整个重新弄过,因此你要有心理准备,未来两年你可能不会常常看到我了。”
珍说:“我很了解他,我知道他工作上一定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且我很高兴他事先告诉我。那个时候的女人一切都是为了丈夫,总是尽一切的努力来帮他。我们不是现代的新女性,我们以丈夫的成就为荣,而他都会让我觉得有参与感。”
安德森升上副总裁的时候,有一次他请珍帮忙计划贝金斯家族团聚的活动,珍在所有房间里都安排了鲜花和一篮水果迎接客人,这也是企业夫人应该要做的事情。
安德森是个细心体帖的男人。一九五二年六月他女儿结婚,在一个乡村俱乐部举行盛大的婚礼。婚礼过后,安德森夫妻邀请了三十个近亲好友到家里去,到凌晨两点半左右,客人开始散了,后来新娘的朋友也来了,家里又热闹起来。他们一直待到清晨五点钟,听唱片、演奏乐器、婆娑起舞。珍说:“安德森跟我说,‘既然我们整个晚上都没睡,而且从现在开始我们得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我想你跟我应该到海边去看日出,作为新生活的开始。’”因此他们就到海边去迎接日出了。
安德森在贝金斯公司能够这样兼顾工作与家庭,但是在福特的麦克纳马拉、利斯或米勒,或是李腾工业的桑顿,却是不可能的。早些年弗洛拉常常担心桑顿工作这么辛苦、压力这么大,恐怕会活不久。后来她在青商会这些场合见识到更多桑顿的同行,才发现事情正好相反,反而是很多做太太的人没有过度活跃的丈夫这么长命,而在老婆死后,那些丈夫当然很快又再娶。她猜想,那些太太大概是因为嫁了个工作狂的丈夫,“无形”压力太大而死的。
这些工作过度的企业修道士——不论在底特律或是其他地方——不但不会折损寿命,似乎反而更能延年益寿。说来真是奇怪,这样的矛盾普遍存在而又是多么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