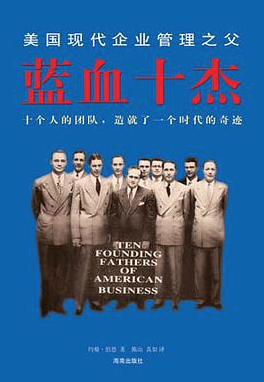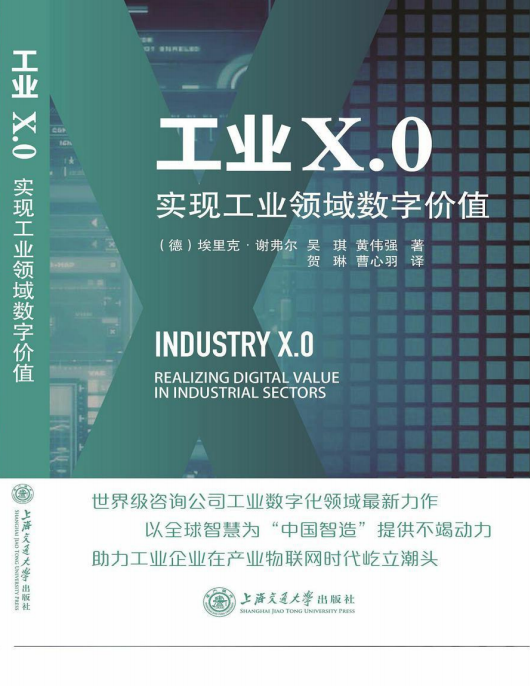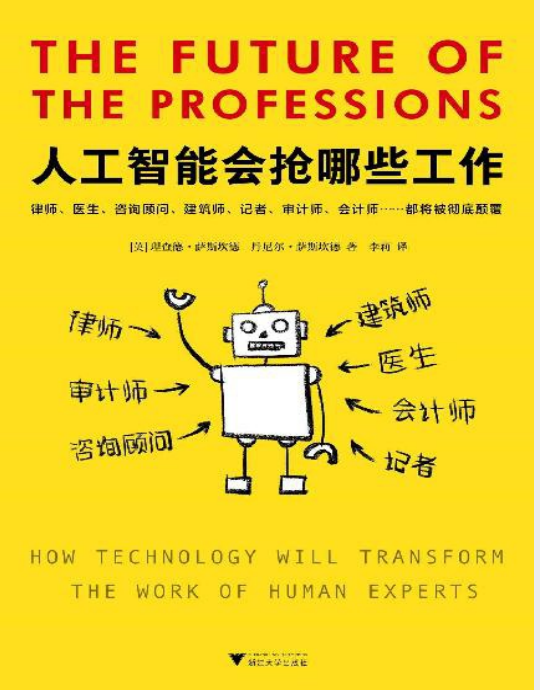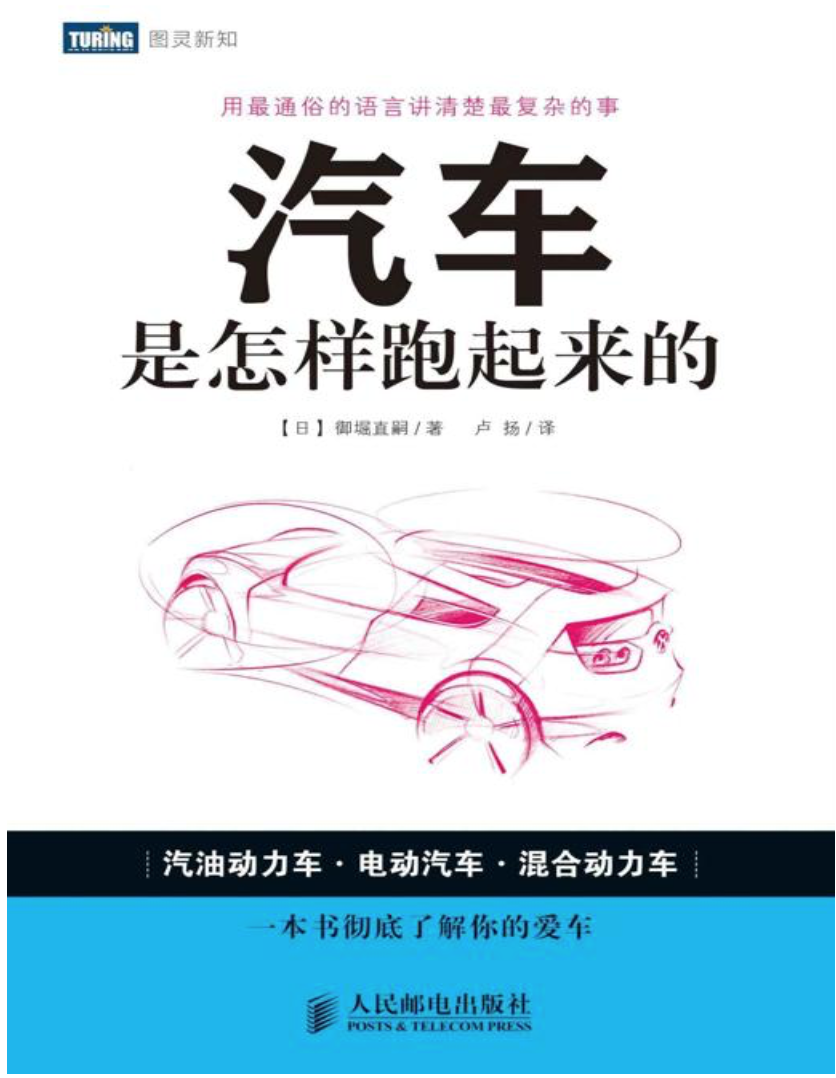11 挑战敌对者
在美国参战的19个月内,福特汽车公司的汽车生产并没有停止。事实上,凭借T型车的新型号,公司在1917年获得了特别大的成功。但是在战争时期更时髦的新T型车大受欢迎,而福特汽车公司于1917年的汽车销量也达到了735017辆,比上一年提高了50%。另外,公司于该年夏季推出的重型卡车(底盘重达1吨)成了军队的“及时雨”。福特卡车加入了欧洲战场上的弹药运输车队,而T型车已在那里服役了一段时间。事实上,“一战”中经过特殊装备的T型车与后来的吉普车最为接近:一种似乎能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的车辆,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
在“一战”岁月中制造所有这些车辆的福特汽车公司工人至少代表了60个不同民族。如果未曾离家的话,福特工厂中的那些辛勤劳作的人可能正在某个远离高地公园的战场上相互屠杀。不过在和平共处的高地公园工厂,“仍然存在一个问题,政府怀疑有德国的支持者正在福特公司工作,”欧内斯特・格里姆・肖回忆说,“公司中有政府派来的人,可能跟我们一样就在工作台上,他们时刻提防着阴谋破坏活动。”
在重组以适应军工生产的强大政府压力下,福特汽车公司的生产员工发现他们正在一种古怪的氛围中工作,每一次无心的错误都会被严格审查以弄清是否为同盟国力量的蓄意破坏。甚至连福特的私人秘书,曾经的银行家欧内斯特・G・利博尔德(Ernest G.Liebold)也受到了怀疑。他出生在北密歇根,但是有一个德国姓氏,而且在那些拼命想寻找日耳曼人的人看来,他的那种简练明快的行为方式正好带有日耳曼味道。战时的一天下午,他开车送福特汽车公司办公室的一位女士回家,但这种善意却遭到了惩罚。因为那位女士把他在车里说的话报告给了政府,“我认为德国人会在溃败之前退出战争。”他的无心评论――尽管不太正确,足以暗示他可能是一个德国的支持者,因为他似乎能获得有关德国意图的信息。这种怀疑令利博尔德非常恼火,尽管最后不了了之。
更令人烦恼的是,强大的外部势力还想让福特汽车公司解雇杰出的卡尔・艾姆德。凭借制图和工具设计方面的天才,艾姆德对公司自由发动机项目的成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他的德国血统使他成了一个明显的靶子。“卡尔・艾姆德和(重工项目主管)查理・哈特纳(Charlie Hartner)都是德国人,我也是德国人,”威廉・克兰说,“负责这个项目(自由发动机)的有12个是德国人,而他们(外部者)说德国人正在阻挠这个项目。”
对一切德国事物的极端排斥是公司内政治压迫的核心――德国人在每个方面都会遭受怀疑。然而,公司所受到的特别注意实际上源自亨利・福特的另一种个人偏见。1916年,当美国派远征军到墨西哥抓捕革命者潘丘・维拉时,亨利・福特表示了强烈反对。更令他恼怒的是,在约翰・潘兴(John Pershing)将军率军跨过边界时,国民警卫队也因军事行动升级而被召集起来。福特断言,美国政府没有权力把一支特遣部队派到他国土地上。对一个一向表示反对战争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立场,但福特所做的不光是发表个人观点那样简单。他也跨过了他自己的敌我边界,声明说任何在墨西哥远征期间加入美国国民警卫队的员工回来以后都不会被接纳,就好像这是公司的一项政策。《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的一篇社论对福特的举动表示了异议,给他贴上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并且建议他不如把自己的工厂搬到墨西哥。“如果福特允许他的这种规定存在下去,我们就会知道,”社论说,“他不仅是一个无知的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敌人,而正是这个国家保护了他的财富。”尽管《芝加哥论坛报》允许福特发表文章否认自己威胁了国民警卫队,但这家报纸的“右翼”出版商罗伯特・R・麦考密克(Robert R.McCormick)仍然拒绝收回上述评论或者为无政府主义的说法道歉。于是,福特起诉了《芝加哥论坛报》,索赔100万美元。福特表示他保留在不对抗政府的前提下与政府意见不合的权利。
这起诉讼在美国的整个参战期内都处于待受理状态,一直到1919年5月才付诸审判。大多数美国人都赞赏福特对军工的贡献,特别是他还承诺不会从中获利,但他的对手们仍然不会轻易相信他。“我觉得亨利・福特是一个寡廉鲜耻又贪婪的伪君子,”麦考密克说,“我认为我对他足够了解。”
1918年,亨利・福特的敌人们开始利用联邦政府对战时飞行器生产的调查打击他。令人意外的是,这次调查的鼓动者是雕刻家格曾・博格勒姆(Gutzon Borglum)。1918年时,他正在考虑开办一家飞行器公司。部分上出于自私的动机,博格勒姆指责说负责自由发动机项目的生产商集团效率低下而且正在牟取不正当利益,并且说服他的朋友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展开了一场调查。围绕自由发动机项目的缓慢进展已经有不少的怀疑和迷惑,雕刻家的话无疑是火上浇油。毕竟,生产在美国参战一年后才开始,这自然会让国人怀疑:没有真正的飞机发动机,只有不劳而获的利润和贪婪的承包商。为了避免公众信心的丧失破坏美国人在参战问题上的团结,威尔逊总统展开了调查。他选择的调查负责人是在1916年大选中败在他手下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这位德高望重的共和党人曾经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作为诸多令人烦恼的后果之一,休斯的调查损害了自由发动机设计者杰西・文森特的商业声誉,他所谓的错误是没有在加入军工项目前卖掉自己的帕卡德汽车公司的股票。由于这点疏忽,文森特在贡献祖国的两年中无意中牟取了55美元的“不正当利益”。就为这个,文森特后来没有得到任何的政府嘉奖,而这种荣誉甚至连他的助手也得到了。不过,选择一本正经的休斯领导这次调查对亨利・福特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
1918年,福特汽车公司很忙,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更忙。在间接与欧洲的同盟国做斗争,直接与公司的几个股东做斗争的同时,亨利・福特还能抽出时间来竞选密歇根州美国参议员的宝座。威尔逊总统就是最早鼓励他竞选的人之一,而数千封来自支持者的信让他下定了决心。无论是福特还是他的共和党对手杜鲁门・H・纽伯里(Truman H.Newberry)都不算积极,但他们背后的政党却把1918年密歇根参议院选举变成了历史上最火爆的竞选战之一。就在纽伯里的班底就亨利・福特在社会问题和战争问题上的立场竭尽歪曲和夸张之能事时,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来到底特律,近距离观察了自由发动机项目。
休斯和他的随行人员特别视察了高地公园,想找出德国人或德裔美国人正在阻挠生产的蛛丝马迹。“休斯委员会视察工厂的那一天,我们正在测试100台发动机”威廉・克兰回忆说,“你听不到你自己的声音,方圆几英里内都是发动机的吼声。”
休斯或许差点儿被震聋,但是他并不满意。相当无情的是,他决定拿卡尔・艾姆德开刀,把这位德国工具设计师的饭碗当成对福特汽车公司忠诚度的检验。“关于艾姆德的表现,我们得不出任何确凿无疑的负面结论,”休斯承认,“但是对管理层中的一些最重要的人来说,让艾姆德交出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职位明显是恰当的。”一时间,艾姆德事件在高地公园闹得满城风雨。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些执行官确实与休斯和休斯的委员会站在了一起。他们的理由是,尽管艾姆德是一个中立的美国公民,尽管他在自由发动机项目中的工作是无可指摘的,但作为公司的一个重要负责人,他可以接触所有的行业和军事文件,所以可以――如果他愿意的话――把这些文件复印并发回德国“老家”。另外一些没有这么强硬但却更加世故的管理人员则认为,艾姆德的职业生涯和安全原则都不如福特汽车公司的声誉重要。因此,如果这个人有可能是一个想搞破坏的间谍,公司最好把他解雇以证明对国家的忠诚,不管他的工作多么出色,多么有价值。
“我还记得那份声称公司设计部雇用了敌国侨民的报告带来了什么后果,”另一位工具设计师威廉・F・皮奥克许多年以后回忆说,“艾姆德受到了猛烈的批评,就因为他是一个德国人。我只能告诉你,那件事几乎把他毁掉。他同我曾共事过的任何美国人一样忠诚。”
艾姆德事件最终于1918年11月3日演化为一场风暴。这一天,《底特律自由新闻》刊登了共和党的一则有关艾姆德的恶毒广告。广告把福特称作“德国佬的情人”,并且声称休斯调查证明亨利・福特本人正在保护工厂中的德国人。当然,亨利・福特是两天后参议院选举的候选人之一,他的许多支持者都认为共和党在这个时候发话绝不是巧合。在这个紧要关头,福特如果拿艾姆德的职业生涯来交换参议院宝座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是不光彩的。他的大多数竞选宣传员都建议他这么做,因为票数多少看来就依赖于此――可能足以使他当选。但是,自1906年亚历山大・马尔科姆森要求汉克・福特制造K型车以来,还没有什么人能替他决定应该怎样做。
候选人福特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骄傲地指出了艾姆德12年内对公司的巨大贡献以及他的革新给自由发动机项目省下的345000美元。私下里,福特对艾姆德说:“如果他们想绞死你,他们得先绞死我。”福特坚定地与艾姆德以及其他一些遭受类似中伤的员工站在一起,对一个雇主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尽管福特经常保护那些他最欣赏的职员,艾姆德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存活下来却有不同的原因:对福特来说,把一个被错误指控为“德国支持者”的人吊死在空中无异于把“无政府主义者”亨利・福特吊死在空中。亨利・福特永远不会承认错误,即使他真的错了;那么在他对的时候,他当然更不会让步。不值得为了赢得选举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亨利・福特正式参选后,密歇根参议员选举立刻成了全美国性的话题。毕竟,他是在美国总统的个人建议下做出决定的。在19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福特不仅公开表示了对威尔逊的支持,还对民主党的加利福尼亚战役捐赠35000美元帮助他们发动了最后时刻的闪电宣传战,而一些权威人士认为,威尔逊之所以能在竞争激烈的加利福尼亚以4000票胜出,从而在选举团选举中侥幸压过共和党人休斯23票,这次闪电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名义上的共和党人,福特也曾在某些问题上公开表示与总统意见相左,但在支持创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以确保未来和平的政府计划时,他俨然又成了一个“威尔逊人”。在不同党派间跳来跳去不是一种聪明的政治表现,福特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宣布他将争取两大党的共同提名。
密歇根州的共和党注册党员比民主党整整多出10万,而州共和党领导人绝不会愿意用这样的多数优势支持任何威尔逊人,不管他在商业上有多么成功。面对福特同时参加两党初选的事实,共和党的领导者们转向了出自耶鲁大学的杜鲁门・H・纽伯里。出身底特律望族的私人投资家纽伯里时年54岁,比亨利・福特年轻一岁。他也与汽车业有联系,早在1902年就曾通过对帕卡德汽车公司投入重金让祖传财富剧增。对福特的获胜希望威胁最大的是,纽伯里曾经在西奥多・罗斯福的任期末担任过海军秘书。这一短暂的经历赋予他军事资历,而这是战争时期的一个极大骄傲,也是亨利・福特的明显劣势。纽伯里击败福特获得了共和党提名,而福特轻松赢得了民主党的初选。这样,两人又一次在美国竞选中相遇。
福特采用了老式战略:他从不亲自露面,也明确表示不会发表演说。他也没有花钱,这与他早些时候的话倒是相符合的。“这些竞选花销都是浪费。”福特曾经在1916年威尔逊竞选总统时这样说。“我不会给任何竞选委员会捐赠一个子儿”――但这是在他资助威尔逊的加利福尼亚闪电战之前。无论如何,福特并没有对自己的参议员竞选投钱,而且也拒绝了民主党的资助。他所做的只是组织了他自己的超党派福特参议员俱乐部(Ford for Senator Club)。在两党初选中,福特这边总共花了335美元,剩下了226美元。
相比之下,杜鲁门・纽伯里仅仅为了在共和党初选中击败福特就花了176568美元。后来,他在参议员选举中的支出达到了50万~100万美元。民主党机器不断利用报纸、传单和集会攻击福特的爱国问题。《美国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 )报道说,在选举日临近时,“每一个可能会施加影响的人都拿到了钱――给个人,给共和党人,给民主党人,只要是可能有用的人都一样;给政治、社会、工业和宗教组织,都一样;给报纸,不光是广告费;替那些从没参加过一英里竞选游行的人结清账单”。
伊利诺伊州的元老级参议员劳伦斯・谢尔曼(Lawrence Sherman)对那次竞选的冷嘲热讽可能是亨利・福特应当承受的,“由于能让他那发热的大脑降降温的更好的冰箱尚未出现,”谢尔曼说,“他治愈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去争夺空余席位。”不过,这位好发牢骚的共和党参议员憎恨的不光是福特这个人,因为他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想说,我认为福特汽车是一种国际害虫。”
这一次,通常较为自由的《纽约时报》对亨利・福特的理解同美国的保守派政治家们也大同小异。《纽约时报》社论版曾经在塞尔登案中支持福特,也曾经对他的日薪5美元政策大加赞誉,但对他的政治野心却表示了迷惑。根据这家报纸的观点,福特在密歇根获胜“将让参议院和汽车行业都出现空缺,而对后者来说,福特先生是不可或缺的”。这就引起了另一个相关问题:亨利・福特是否愿意让他的公司缺了他,甚至是否能忍受居住在华盛顿而远离他的公司。
当选举日临近,纽伯里的人对埃兹尔・福特逃避兵役的攻击开始升级。由于福特没有就卡尔・艾姆德和其他一些敌国侨民的问题回应共和党人,“最初的指责……充斥在全州那些敌对报纸的星期一版上,”历史学家戴维・刘易斯说,“结果,在星期二投票的千万选民只了解那些谴责,没听到任何抗辩。”福特也批判了对艾姆德和高地公园中的其他一些外国工人的歧视,但只是在选举日当天才在大多数密歇根报纸上刊出,而当选民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大多已经投完了票。因此可以说,是福特允许纽伯里阵营的卑鄙行径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影响力。
双方形势十分接近,计票工作花去了三天时间。结果,两大党候选人共得432541票,杜鲁门・纽伯里以7567票的优势击败了福特。失败者目瞪口呆,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相信他的个人影响力足以抵抗对他本人及其同伴的任何攻击。选举日后第9天――也就是“一战”结束后第5天,自我中心主义遭受重创的亨利・福特发表了一份声明,发誓他将永远脱离让人“掉进沟里,陷入泥泞”的那种政治。
福特还特别表达了他对对手竞选花销的憎恶――这个问题在85年后仍然是国会的争论核心之一。“究竟有多少钱用于确保那个参议院席位只有良心知道,”福特说,“如果他们愿意花176000美元去获得一个小小的提名,他们也会愿意花1.76亿美元去控制整个国家。这就是危险所在。”
人们认为,被政治领域拒之门外的亨利・福特肯定会灰溜溜地逃回自己的圈子。确实,福特回到了制造和改进拖拉机的事务,但绝不是夹着尾巴逃回去的。这个密歇根最富裕的人从不羞于失败,不管在外人看来有多么难为情。在福特眼中,这次参议员竞选确实是一个失败,但却是选举漏洞的一个失败。当然,他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美国的州内选举是多么容易用钱买赢的人。正因这一弊端,密歇根州于1918年颁布一项法律,为议员初选设定了3750美元的花销上限――除了广告费用。这远远低于当时联邦法律所规定的10000美元的上限。纽伯里的竞选委员会明显违反了州和联邦法律,正在因共和党初选中的过度支出而遭受炮轰。杜鲁门・纽伯里坚持认为他没有做错什么,因为竞选费用中没有一分钱是他自己的。他狡猾地使用了一种直到今天还在困扰竞选财政改革的借口:其他人怎么花钱是他无法控制的。
当然,亨利・福特怎么花钱也是纽伯里无法控制的。在朋友哈维・费尔斯通的协助下,这位怀恨在心的汽车大亨雇了大约100个私人调查员在全州范围内搜寻竞选舞弊的证据。这支队伍用了4个月的时间挖掘出了足够多的肮脏交易――多得以至于纽伯里的参议院席位还没坐热,两纸独立诉状便已送达,一份要求密歇根州重新计票,另一份要求开除这位道德败坏的新参议员。这两个招数以及迫使纽伯里辞职的类似行动都失败了。但在亨利・福特的脑子里,他的律师和私人侦探大军还有其他一些任务,而现在他已经检验了这支大军的力量。
福特对福特汽车公司最大的个人贡献,可能就是他在提高产量上的坚定态度。当有关公司的其他所有事情都来自众人的工作,吹响工厂扩张的号角却是他一个人的功绩。无疑,惊人的销售速度鼓励了他,在高地公园休息室里转来转去只为多弄几辆T型车的外地经销商也是他的动力。福特的计划基于一个高明的公式:产量提高会让价格下降,而价格下降会让销量提高。当然,这样一种策略会逐出竞争者――1914年年末时T型车已经是唯一一款价格在500美元以下的汽车。然而,亨利・福特真正的与众不同之处却在于,他一年到头地加速提高产量实际上是在冒整个企业可能因短期的销量下降而崩溃的风险。
大多数制造商都对“美国能买多少辆汽车”的问题非常重视。毕竟,扩张只能是对需求的成比例回应是当时的传统认识。福特汽车公司是唯一一个认为产量提高能预示销量提高,而且是大提高的企业。内在风险正存在于此。如果需求下降,工厂那不断提高的产量就不再是福特主义的闪光典范,而像是一家疯狂公司的疯狂表现。
福特对此并无担心。他关心的只是如何降低T型车的价格。其他所有事情都得遵从这个目标。由于高地公园的效率和产量潜力都已发挥到极致,福特开始准备在荣格河地区建立一家新工厂。高地公园工厂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工厂,但新工厂将比高地公园还要大。实际上,按照福特的设想,新工厂将成为全世界所有类型的所有工厂中的头号巨人。
1916年,亨利・福特第一次产生了在荣格河建立一家最先进冶炼厂(用于混合或精炼矿石)的想法。为实现这个宏伟计划,福特汽车公司需要资金,而数千万美元的年利润是现成的资金。在早些年,福特汽车公司会把大约一半的净利润用于分红。但从1915年开始,公司转向了新策略(得到《密歇根州公司法》的支持)――每月拿出相当于公司资本5%的利润来进行分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公司通过一种老掉牙的资产评估方式所计算出的资本仅是其实际资本的1/50:200万美元,而高地公园工厂一天就能生产价值200万美元的汽车。不过,即便按照这种低得荒唐的资产估价,公司的分红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仍然是颇为丰厚的,1919年,最大股东亨利・福特本人得到了大约50万美元。尽管福特已经像其他股东一样习惯于拿到10倍于现在的分红,但同样像其他股东一样,以前年度的利润已经让他拥有了足够的财富――几百倍于1903年公司成立时任何人的想象。正是由于囊中充裕,大多数股东并没有反对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张的新分红方法。而当时任底特律警察局局长的第二大股东詹姆斯・卡曾斯则因警务繁忙而没能提出任何抗议,他姐姐罗塞塔・卡曾斯・豪斯(Rosetta Couzens Hauss)的那点儿投资自然也只能随大溜了。霍勒斯・拉克姆、约翰・安德森以及约翰・S・格雷的继承人都表示满意。这样,只剩下道奇兄弟在那里吵闹不休了。
那时候,约翰・道奇和霍勒斯・道奇已经开始生产他们自己的汽车。有点儿像T型车老大哥的道奇车卖得相当好,从第一个完整生产年1915年开始一直是美国五大畅销车之一。在1916年的那次被亨利・福特狠批一通的远征中,“黑杰克”(Black Jack)潘兴将军就是用道奇车队在墨西哥的险峻峡谷中追逐潘丘・维拉的(他开的是T型车),这为道奇车赢得了永远的声誉。道奇兄弟公司的汽车长久不衰,产量一直在迅速上升,到1919年已经超过了100000辆。不过,它以及其他品牌仍然无法与福特汽车相提并论――这一年的T型车销量是521599辆。
约翰和霍勒斯总共握有福特汽车公司10%的股份。单单1914年,他们就获得了122万美元的红利――这是他们连续第三次拿到7位数分红,而出于两个原因,他们希望这样的巨额回报能继续下去。首先,为了不断发展自己的汽车公司,他们需要尽可能多的资金;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他们确信亨利・福特把这么多公司的利润投在荣格工厂的大胆计划中是在拿公司的生存能力冒险。
1916年11月2日,约翰和霍勒斯起诉了福特汽车公司董事亨利・福特、埃兹尔・福特、霍勒斯・拉克姆和弗兰克・克林根史密斯,控告他们损害了股东的利益。特别地,道奇兄弟要求密歇根州巡回法庭勒令福特汽车公司永远把3/4的利润用于分红,禁止公司投钱在属亨利・福特个人所有的荣格河地盘修建冶炼工厂或其他任何东西。道奇兄弟还反对(至少从这桩官司来看)日薪5美元和T型车的削价,但头两项指控才是事关福特汽车公司未来的斗争焦点。
正如阿伦・内文斯所说,约翰和霍勒斯反对福特汽车公司以区区200万美元的虚假资产评估为基础计算分红是正当的。“事实上,”他和弗兰克・欧内斯特・希尔在《福特:扩张和挑战》(Ford:Expansion and Challenge,1915~1933 )一书中写道,“1916年7月31日的年度报告显示,公司上一年的净利润几乎达到了6000万美元,现金结余也超过了5200万美元。在通常情况下,公司至少应该宣布2500万美元的分红。”
案子最终于1917年6月开庭审理,道奇兄弟的律师之一威廉・卡彭特(William Carpenter)对巡回法院法官描述了他的委托人所遭受的不公。“福特先生,”卡彭特说,“已经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所有的钱。他的野心是雇用尽可能多的人,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出售汽车,而应该对股东尽到的义务,他一点儿也不考虑。1916年,他可以挣得6000万~7500万美元,他却只挣了2800万。当其他所有的汽车都在提价,福特为什么要降价?就算他只想保住在汽车世界的领导地位,难道他一定要降价吗?他真正的愿望是做大众恩人。他想以股东的损失换取自己的荣誉。”
“我们要求福特先生以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经营公司,”卡彭特继续说,“当一个企业只是扩张自己,不去赚取利润,它就是在非法经营。”尽管今天的许多股份公司,特别是发展迅速的那些行业中的股份公司,都会选择牺牲股东分红而把全部或大多数利润用于再投资,但在1910年,这样的方式是闻所未闻的。如果亨利・福特是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而不是头25年中经营他的公司,他或许不会有消灭外部持股者的动机。这样想来,在减少分红这一点上,福特是远超前于他那个时代的,所以他承受着要求他与当时的公司规范同步的压力。
道奇兄弟还指出,在荣格河修建冶炼厂超出了福特汽车公司的章程。公司是为制造汽车而成立的,而根据密歇根州的法律,修建像冶炼厂这样的炼钢设施属于一个不同的,而且是相当特殊的法律条款。对亨利・福特当时的计划来说,这一点同他对发展的强调一样重要,而他想在荣格河修建什么样的工厂可以表明他为公司设定的发展方向。同汽车业的专业化趋势截然相反的是,福特汽车公司的目标是把更多供应商的产品纳入自己的生产范围。也就是说,福特汽车公司想用自己的树木、矿石和橡胶工厂生产全部的木材、金属和轮胎,然后再用这些材料生产自己的汽车。
一审裁决支持了道奇兄弟对分红问题的意见,但驳回了他们的其他诉求。法庭命令福特汽车公司立即支付19275385美元的特别红利,并且调整分红政策以保证50%的公司利润能回到股东手中。另外,巡回法庭裁定在荣格河修建冶炼厂确实与福特汽车公司的章程不符。自然,福特汽车公司提起了上诉,这至少会把上述要求的执行拖延到1919年。
然后,亨利・福特于1918年11月投下了重磅炸弹。他宣布他将在年末辞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的职务。“我对未来很感兴趣,不光是我的祖国的未来,还有全世界的未来,”公司办公室所发表的官方声明说,“我的脑子里有能给所有人带来好处的明确的观念和理想。我想让它们不经混淆、歪曲和误传地被公众知晓。”简言之,福特的最后一份职业将是“报纸出版商”。这种新雄心的表现舞台就是他刚刚买下的周报《迪尔伯恩独立报》(Dearborn Independent ,以下简称《独立报》)。在前任所有者的经营下,《独立报》只是一家默默无闻的小镇报纸,但亨利・福特对它的未来已经是胸有成竹。“我一向对微不足道的开端抱有信心,”声明继续说,“因此我要接管和建设这家家乡小报。”一般的猜测是,福特是吸取了密歇根参议员竞选的教训,想把这家报纸当作他开启政治生涯新阶段的平台。或许,他的目的地是1920年的白宫。不管亨利・福特的真实目的如何,他的辞职决定在汽车行业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作为接班人,25岁的埃兹尔・福特被父亲任命为新总裁,掌管起这家价值2.5亿美元的企业。在亨利・福特的余生之中,埃兹尔一直是公司的总裁。
这次巨变让福特汽车公司拥有了(至少是名义上拥有了)一个更有能力,当然也更有理性的领导人。本性善良的埃兹尔・福特与他这个年龄的大多数富家子弟都大为不同,他对待公司官员这一角色与对待有家男人这一新角色一样认真。在亨利二世之后,他和埃莉诺又先后生了三个孩子:本森(Benson)、约瑟芬(Josephine)和威廉(William)。
让我们设想一下埃兹尔在接受开始于1919年年初的新角色时有何感受。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他知道父亲是一个古怪无常的人,但他一定对自己接任总裁充满信心,因此一定会对摆在眼前的机会感到激动。不会有什么生活比现在的生活更加美好了。但对埃兹尔来说非常不幸的是,事情最终变糟了。无论如何,父亲和儿子的角色变化并没有马上发生,一切皆起因于那年冬天福特全家在洛杉矶附近的加利福尼亚阿尔塔德纳所休的一次长假。
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是福特家在阿尔塔德纳的新邻居之一,出于对工业改革的兴趣,辛克莱自然很想了解亨利・福特,所以他在阿尔塔德纳数次拜访了福特。根据辛克莱所说,福特家(亨利、克拉拉、埃兹尔、埃莉诺和亨利二世)所租的房子普通得令人吃惊,第一次访问时他就发现伟大的工业家和他的儿子“正在车库中,他们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能搞设计的小工厂――亨利在老巴格利大街就是这么做的,那时候埃兹尔还没出生”。
“在这个地方,”辛克莱继续说,“他们见到了一个旧化油器的一部分,但这东西出自什么车辆,他们并不知道……亨利和埃兹尔对上面的一个孔着了迷,因为他们想不出这个孔的用途是什么。他们把它展示给我,询问我的想法。但当时,我正骑在一辆自行车上,而且根本不知道化油器是什么玩意儿。”
但辛克莱还是成功地与老福特畅谈了美国的商业系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这位公然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作家提出,如果福特汽车公司能归“人民”所有,纵使亨利・福特仍然担任首领,公司也更有可能成就大事。然而,福特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一群匿名者叽叽喳喳地告诉他应该去做什么。
1919年2月7日,司法系统做了福特最不想看到的事:告诉他应该去做什么。密歇根州高级法院宣布了对“约翰・F・道奇和霍勒斯・E・道奇对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和其他人”一案的最终裁决结果。这只是一个局部改判,虽然把在荣格河修建冶炼厂归入了福特汽车公司的权利范围,但也再次支持了道奇兄弟对公平分红的定义和要求。尽管公司已经在1919年前两个月重新使用了公平的普通分红方式,法庭命令公司追溯支付过去的红利仍然让亨利・福特大为光火。不管怎么样,在亨利・福特仍待在阿尔塔德纳的时候,公司财务主管弗兰克・克林根史密斯已经开始准备向股东支付法庭要求的1930万美元。
“亨利・福特今年55岁,”厄普顿・辛克莱在加利福尼亚的那个冬天写道,“身材修长,头发灰白,思维敏捷,行为方式简洁有力。他那又长又瘦的双手从不休息,总是在做些什么。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不会装腔作势,并没有被他的巨大成功改变。大概是没有接受过语法教育的原因,他的话语中充满了中西部老百姓的那种怪癖的说法。他从来就不曾学会理论研究,当碰到一种理论的时候,他会迫不及待地回到现实,就像野兔逃回洞窟一样。”
“他所知道的那些东西,”辛克莱总结说,“都是从实践中学来的,而且如果他想再知道一些东西,他仍然会采用同样的方式。”
3月6日,亨利・福特宣布他正在组建一家新汽车公司。不带委婉语调,他承认他这样做是因为对高级法院的裁决感到厌恶,他认为,法院已经逼迫他以违背自己最佳判断的方式分配了福特汽车公司的资金。福特的新计划让公司的执行官和股东们大吃一惊,而且不到几个星期他们就会知道,亨利和埃兹尔在阿尔塔德纳所做的不光是在车库里摆弄那个旧化油器。5天之后,轮到埃兹尔做出声明了:他和他的父亲都将彻底撤出福特汽车公司。
道奇兄弟的律师之一埃利奥特・D・史蒂文森(Elliott D.Stevenson)指出,合同不允许亨利・福特离开福特汽车公司去开办一家新汽车公司。仍然对自己在分红案中的胜利洋洋自得的史蒂文森可能希望用另一场争斗来为个人声誉锦上添花。然而,福特汽车公司的许多经销商却开始感到恐慌,因为新公司一旦成立,他们的利润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有关高地公园未来命运的流言迅速出现。因为没有福特总裁的福特汽车公司这一概念本身似乎就是荒唐的。有一种说法是,通用汽车公司想要收购它的对手,把高地公园并入它那迅速成长的汽车和零部件制造企业集团中。
通用汽车就像以威廉・杜兰特的股票操控为地基的纸房子,据说它以前就曾试图收购福特汽车公司。1909年秋季,就在通用汽车还是个一岁娃娃的时候,杜兰特就用尽个人魅力想要说服亨利・福特和詹姆斯・卡曾斯以800万美元的价格出让他们的福特汽车公司股份。但交易因杜兰特的华尔街投资者们拒绝为此融资而成为泡影。不过到1919年,说通用汽车会考虑购买福特汽车公司已经成了一个笑话。杜兰特的过度扩张已经让他面临着失去整个公司的危险――事实上,他下一年就会被取代。然而,福特汽车公司可能会被出售的传言反映了公司的不稳定,而这正是亨利・福特的意图所在。无疑,投资者倾向于回避不稳定性,到7月份,福特汽车公司的大多数股东都做好了出售股份的准备。
数额如此接近的股份之间本来不易一次性完成交易。但依照埃兹尔・福特的一个商界老友对他的建议,福特父子通过波士顿的一家金融公司老殖民地信托公司(Old Colony Trust Company)完成了交易。老殖民地公司负责所有的谈判,亨利・福特只做出了一个规定:如果他不能买到所有的股份,他一点儿股份也不会买。福特汽车公司共发行了20000股股份,其中亨利・福特有11400股,埃兹尔有300股。剩余的8300股分属于詹姆斯・卡曾斯(2180股)、道奇兄弟(各1000股)、约翰・S・格雷产业(2100股)以及约翰・安德森和霍勒斯・拉克姆两位律师(各1000股)。根据道奇兄弟诉讼案中的资产评估,福特汽车公司的每1股股份价值12500美元。而16年前公司成立时,合伙人们认购1股的现金支出只是100美元。
曾于1903年以25美元的价格为福特汽车公司起草成立文件的安德森和拉克姆在1919年各自以125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股票,而最初,他们每人只花了5000美元认购那些股票。相比之下,曾把自己的两层麦克大街木工工厂租给福特汽车公司的约翰・施特雷劳同样是在1903年购买了5000美元的股份,但仅仅两年之后他就以250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这些股份。如果福特汽车公司之父亚历山大・Y・马尔科姆森没有早早放弃自己所持的1/4的福特股份,没有在1906年以175000美元把它们卖给亨利・福特,那么在1919年他会得到6300万美元。
那些持有股份的人确实又发了一笔横财。道奇兄弟每人得到1250万美元;约翰・格雷的后人得到2625万美元。詹姆斯・卡曾斯,1919年时的底特律市市长,提出了一个稍高一点儿的售价,但这主要是为了迫使福特承认他对公司的特殊贡献。他成功了,与老殖民地公司与其他股东的交易不同,他以每股13000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以及姐姐的股份。卡曾斯净赚2931万美元,罗塞塔・卡曾斯・豪斯因托管给弟弟的那100美元而入账262000美元多一点。
不过,对这宗大手笔交易,没有一个人比亨利・福特更满意,因为他最终变成了福特汽车公司的唯一拥有者。根据一篇报道,亨利・福特得到其他所有股东都同意把股份卖给他的好消息是在7月的一个早晨,当时,他正要进入法庭,继续与被控名誉损害的《芝加哥论坛报》对簿公堂。他可能已经知道交易顺利完成了,但就在他走上法院台阶时,一封正式通报这一消息的电报才送到他手中。第二天,全世界的报纸都报道了当时的情景。由于所有的交易都是以埃兹尔的名义进行的,亨利・福特在法庭中的即席新闻发布会上诙谐地说,“哦,如果埃兹尔买下了公司,我会帮他。”
在亨利・福特彻底控制了福特汽车公司之后,他又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购买股份共花了大约1.06亿美元,为此福特不得不借了7500万美元。事实上,巨额借款是这次胜利的唯一阴影。在此之前,亨利・福特从未沾过信贷的边儿,甚至连抵押借款的记录也没有。更糟糕的是,贷款者都是他瞧不上眼的东部银行家。不过,福特相信偿还这笔巨款很容易,他要做的所有事就是不断出售T型车,而这一点从来就不是问题。
很明显,福特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获得公司的完全控制权。他愿意为此付出的成本不光是一个财务问题,还是一个职业问题,甚至还是一个私人问题。他疏远其他人的行动从清除马尔科姆森就已开始,到詹姆斯・卡曾斯离开时达到了顶峰,驱逐其他外部股东只是一个延续。更能说明问题也更加有害的是,福特也接受了1919年3月哈罗德・威尔斯的辞职。从一开始,威尔斯就凭一己之力为福特汽车公司设定了长久以来闻名遐迩的高技术标准。实际上,许多与威尔斯同时代的人,偶尔也包括亨利・福特,都承认他是T型车背后的真正天才。威尔斯监控了T型车的最初设计和头10年中的每一次改进,确保了大规模生产没有以质量的下降为代价。但尽管T型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威尔斯的不满情绪却越来越强烈。事实上,早在1912年,威尔斯、查尔斯・索伦森以及福特汽车公司设计部门的其他人就已经开始劝说亨利・福特设计一种新车型,或至少是升级和改进T型车。
为了点燃自己的热情,激起老板的兴趣,威尔斯和他的机械师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设计出了一种全新的T型车,准备在福特全家从1912年的欧洲夏季之旅返回后展示给亨利・福特看。当福特出人意料地来到修理厂看到了那种车,乔治・布朗正巧在那里。在老板的询问之下,威尔斯煞费口舌地解释说新车型是计划投入生产的。布朗远远地看到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
“福特把手放在口袋里,围着汽车转了三四圈,”布朗回忆说,“非常仔细地观察它。他转到车的左边,伸出手来,抓住车门猛力一拽,咣一声!他居然把车门扯下来了!他从那里跳上车,咣!另一边的门也下来了。又是咣一声,挡风玻璃也掉了。然后他跳到后座,又开始对付车顶。他用鞋的后跟把车顶踹破了。总之,他竭尽所能地想把那辆车毁掉。”
“新”福特就这样夭折了。亨利・福特对威尔斯和其他一些人的训斥结束了设计其他车型的任何倾向,至少是暂时结束了。福特认为T型车拥有完美的基本结构,他反对彻底的重新设计,但并不反对T型车的变化。车身样式上可以增减,零部件也会得到改进,但T型车独一无二的地位不容触动。在“一战”结束后,亨利・福特对“大众型汽车”的推崇甚至还超过了战前。
到1919年,威尔斯已经受够了亨利・福特,因为他和他的技术队伍的才能正受着令人窒息的控制。另外,亨利・福特也受够了,因为他得把自己得到的分红留1/10给首席设计师,再加上80000美元的年薪,哈罗德・威尔斯的年收入达到了50万美元。1903年,福特为吸引威尔斯加盟而与他达成的私下协议最终使他成了福特汽车公司报酬最高的员工。福特早就不再认为自己是这项交易的有利一方,因此,正像历史学家基思・斯沃德所写,“急于在不引起诉讼的情况下终止这个老协议的亨利・福特采用了一种暧昧的策略。1919年的某个时候,威尔斯被架空了。没有任何工作要经他之手。他还需述职,但他的职责已经是虚无缥缈,就像他已经死了一样。刚愎自大而且已经对福特枷锁感到厌烦的威尔斯是无法容忍这种状况的。”
确实,公司的设计天才同总裁一样骄傲。“我在威尔斯先生手下工作,”冶金师约翰・万德西解释说,“他在意的只是他自己,不是福特汽车公司或其他人。”“这可能就是福特先生让他离开的原因。”万德西补充说。实际上威尔斯是自己决定离开的。退出后没多久,哈罗德・威尔斯在同样刚刚离开福特汽车公司的约翰・R・李的帮助下开办了自己的汽车公司。20世纪20年代最时髦的豪华车之一威尔斯-圣克莱尔就是他们两人的杰作。
要想了解世界上最重要的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你必须首先了解亨利・福特。通常,他是借助代笔人或新闻记者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因此公众很少有机会直接从他那里听到未加过滤也未经修饰的话。但就在他(和埃兹尔)完全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之时,他也开始为《芝加哥论坛报》名誉侵害案出庭作证。于是公众从他的证词中第一次了解到了他的另一面。
庭审在密歇根克莱门茨山一个宁静的小村庄进行。亨利・福特的指控是,《芝加哥论坛报》在1916年的社论中把他称为“无知的理想主义者”损害了他的名誉。以此为由,他索赔100万美元。然而,与其说这场官司与《芝加哥论坛报》以及它那篇有争议的社论有关,不如说它是展示声望和财富都已达到新顶峰的新亨利・福特的一个机会。大多数重要报纸都刊登了亨利・福特的全证词:对这位百万富翁的一次难得一见的原版访谈录。
身着暗黑色套装,福特舒舒服服地躺在结实的木椅中,双腿偶尔交叉,偶尔向前伸出。他一直没有坐直、放平双脚或摆出其他任何的自我保护性僵硬姿态。毕竟,他不是被告,而是原告。而且正像全世界将要了解到的,他还是一个惜字如金的人。
“你对历史有什么了解?你读过历史吗?”《芝加哥论坛报》的辩护律师埃利奥特・史蒂文森大声说道。三年以前,他就曾代表道奇兄弟对付福特汽车公司。
“相当了解。”福特悠闲地说了句反话。
“那么,《芝加哥论坛报》社论说你是‘无知的理想主义者’,是对的了?”史蒂文森继续发难。
“哦,我承认我对某些事情比较无知。我对艺术就一无所知。”福特回答说。
“对历史了解不多?”
“不多。”
“如果你不懂历史,你有什么资格评论战备会带来什么后果?”
“我生活在现在。”福特回避了这个问题。
“你对这届政府的基本原则也一无所知?”
“我猜宪法就是基本原则。”
“你知道‘政府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意思吗?”史蒂文森紧咬不放。
“不明白你的意思。”福特说。
“政府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是你。”福特回答说。
“你知道的就是这个?”律师问。
“这是一个很长的话题。”原告说。
为了证明亨利・福特确实是《芝加哥论坛报》所说的“无知的理想主义者”,史蒂文森继续从一般知识特别是美国历史知识入手为难汽车大亨。于是,整个国家都了解到,他们的头号工业家不光对1812年的战争为何爆发一无所知(当然,这场战争远在他出生之前),甚至对1898年2月美国战舰缅因号(Maine)在哈瓦那港口被炸沉的事情也只是略有耳闻,而那一年他已经34岁了。后面的问题还揭示出了福特对革命战争的无知,因为他把叛国的将军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说成了一个作家。然而,尽管亨利・福特在高中级别的历史问题上屡屡犯错,从理发店到餐厅,全美各地各个角落都有人支持这位汽车制造商。对他们来说,亨利・福特在本行业中做得怎么样才是最重要的。正像福特本人所说,如果一个人有能力雇人告诉他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是何许人也,他自己并不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一旦亨利・福特把话题限制在汽车制造,辩护方对他的大肆羞辱将会变得不得体,也不公平。但《芝加哥论坛报》的律师不光是在质问一个汽车制造商。1915~1917年,福特私人雇用的“和平秘书”西奥多・德拉维涅(Theodore Delavigne)撰写了一系列全国闻名的报纸专栏文章批评战备和战争,而福特在这些文章中全都署了名。埃利奥特・史蒂文森很清楚,他是在检验这位自我标榜的公众教育家的资格。法庭上的焦点只是《芝加哥论坛报》把福特称作“无知的理想主义者”是否合适,但史蒂文森的问题却超出了这个范围。
“你想教育美国人民?”辩方律师问。
“我想让他们去思考。”亨利・福特纠正说。
“告诉美国人民在危急时刻如何履行公民的义务?”
“告诉人们他们是怎么被利用的。”
“你知道吗,”史蒂文森想压制住他的对手,“在试图教育别人之前,应该先教育好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也接受了一定的教育。”福特咕哝了一句。这话有些牵强。
史蒂文森可能击中了福特的要害。作为一个想到哪说到哪的哲学家,福特经常随心所欲地对身边的人发表言论,不管自己的话有多么过分。他明显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在其他人的认识要胜过他的公众问题领域,他的个人直觉和经验无法同真正的知识相对抗。他曾在1916年5月对《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记者说“历史或多或少是废话”,但他错了――一个地位如此之高的人必须要懂历史,否则,他的观点就不会像他的影响力那样拥有牢固的根基。
在克莱门茨山的庭审过程中,美国公众了解了有关T型车创造者的许多事情。福特从没犯过法,除了违章超速。他读文章一般仅限于标题,而且作为一个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他对缴纳所得税从无异议。“不管它有多高,”他这样评价税率水平,“我的钱越少,我的麻烦也越少。”如此经典的朴素主义言论让亨利・福特这个大富翁贴近了工人阶级的心,就像他给人留下的另一种有些难堪的印象一样:在作证过程中,辩方频繁地要求他大声朗读一些文件,他每一次都会表示反对,通常会以忘记带“眼镜”为由。这不禁让人怀疑伟大的亨利・福特读不了文件――这也是事实。7月22日,史蒂文森不再兜圈子。
“福特先生,”他胸有成竹地说,“我有些犹豫,但为了对你公平,我应该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在那些呈交给你的东西当中,有些你不愿意读,我觉得你已经制造了你无法阅读的印象――你想略过那些文件吗?”
“是的,你可以略过,”福特回答说,“我读东西的速度不快,还患有花粉症,我在阅读方面不太好。”
“你想把这样的印象留在这里吗?”史蒂文森逼问。
“我不想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但我阅读速度不快。”福特说。
“你究竟会不会读?”
“我会读。”福特声明。
“你想试一试吗?”
“不,先生。”
“你宁肯给人留下那种印象?”
“我宁肯如此。”福特下了结论。于是这种印象就留下了。
一天接一天,主要由本地农场主组成的陪审团听取了亨利・福特的全部证词。在对阵双方结束了胜负难料的辩论之后,农场主们没花多少时间就得出了结论:《芝加哥论坛报》把亨利・福特称作无政府主义者确实侵害了他的名誉。不管这12位陪审员和全世界的其他人在亨利・福特身上发现了哪些事实,能说明他是一个无知的理想主义者的证据肯定不在其中。不过,法庭把100万美元的赔款额压缩到了象征性的6美分。
《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 )拿判决结果开起了玩笑。“陪审团认定他不是一个无知的理想主义者,”该报发表社论说,“但是被告对他的名誉损害程度不超过6美分。”《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 )则认为,整个官司对《芝加哥论坛报》和被它污蔑的汽车制造商来说都是一个大大的免费广告。
不管怎么说,福特对这次名誉损害事件的懊恼到1919年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在美国(包括亨利・福特和他的公司)的帮助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大约一年前就以协约国的胜利结束了。
当然,知识分子和工业家之间的争论并没有结束,正像权威评论家乔治・F・威尔(George F.Will)2002年7月14日在他的辛迪加报业专栏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许多知识分子鄙视市场,因为市场在没有知识分子监控的情况下依然运转良好,”威尔写道,“这是一种忘恩负义的鄙视:正是那些让市场富有效率的庸俗的人(知识分子们这样看他们)让社会养得起知识分子阶层。就像(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由于知识分子不是廉价物,在现代企业系统崛起之前,没有什么社会能拥有很多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这些教授对亨利・福特的感激应该远远超过对带有他的名字、分撒他的财产的那个基金会的感激。’”
像现在一样,亨利・福特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们也想把他归入合适的位置:工业英雄。但他并没有满足于做一个工业家。从克莱门茨山的法庭中领悟到他有权捍卫自己的观点后,福特加快了传播这些观点的计划。结果就是《迪尔伯恩独立报》以及它所珩生出的一些书籍。然而,这些东西又让“无知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最糟糕的那种无知的犬儒主义者。也许在那些从不相信他的和平主义滑稽标签的人看来,他一直就是这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