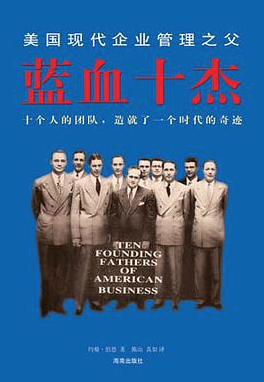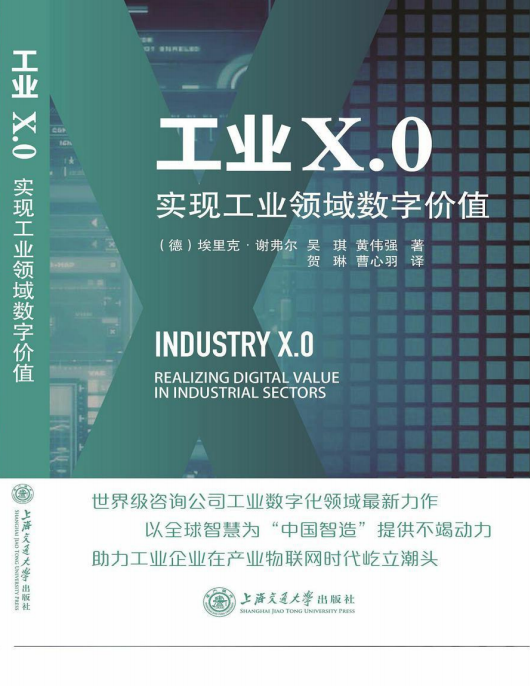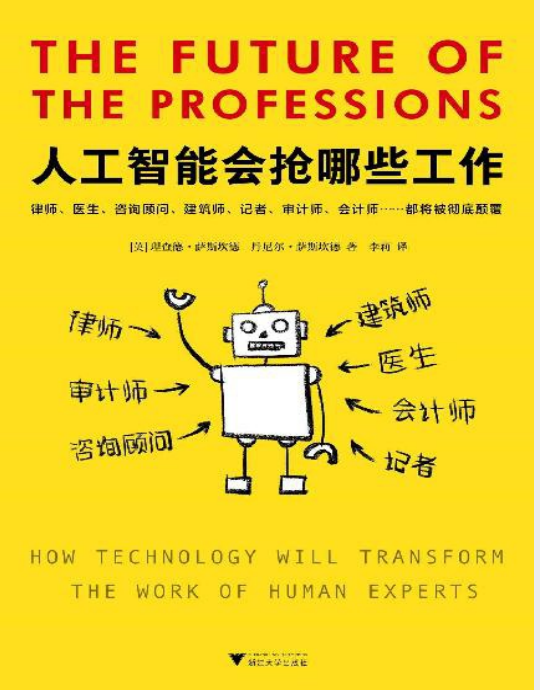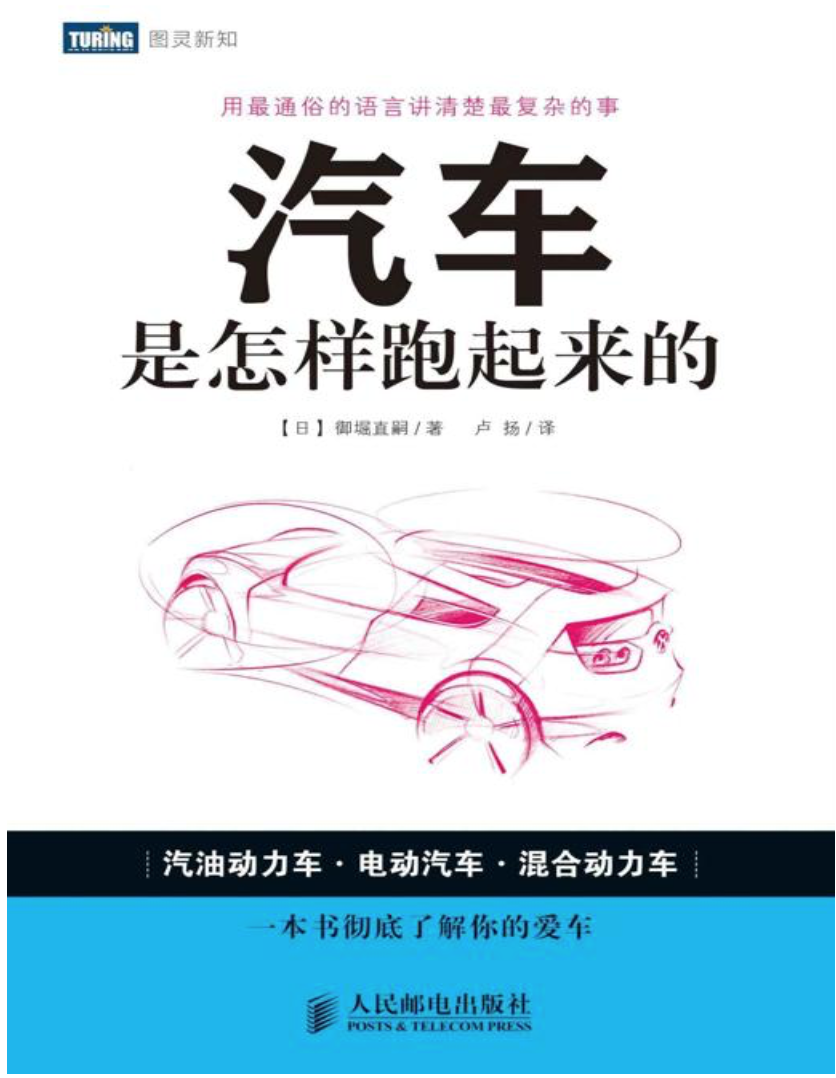2 拿破仑再世桑顿
知识就是力量。而在这片混乱中,我们将是唯一有知识的人,其他人只能瞎猜。
——桑顿上校
其实,多年来,桑顿上校一直都一帆风顺。在华盛顿,他听不见大家背后常叫他“拿破仑再世”。这个绰号多少说出他不惧权威、迫切想掌握生命里每一件事的个性,但是也显示出作战部里的人对他的不满。
有一次,桑顿上校发现一名高阶将领对于飞机产量做了不实的报告,他毫不犹豫地给他难堪——毫不考虑班奈特·伊·梅那中将的官阶,远高过他。“你那些数字有错误,”桑顿上校拖着德州西部口音向梅耶挑战,“这些数字比无中生有还要离谱!”
梅耶将军老羞成怒,立即反击说:“你要是调到我的手下,我一定把你送军事审判!”
“将军,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那我也真该受军事审判了。”桑顿上校平静地反驳。
军中的官僚,愈来愈多人发誓要在战争结束以前把桑顿上校搞下来,梅耶也是其中一个,却从来没有找到机会。这个冲突过后没几天,梅耶所负责的机务报告,整个转移给桑顿上校在华府日益扩大的统计管制处。这次战胜官僚,是年轻的桑顿上校在战时最具戏剧性的胜利之一,他把握住这个机会,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空军,更建立起他自己的权力基础。
崭露头角
“拿破仑再世”的军事帝国,最初不过是陆军航空队的一个小组,由一些知识分子和有企业头脑的人所组成,外人也弄不清楚他们是干什么的。到二次大战结束时,桑顿手下有三千名在哈佛商学院受过训的优秀军官和一万五千名后勤人员,听他指挥调度,统计管制处有六十六个遍布全球的驻外单位,拥有全球最大的中央控制计算机设备和独立的电传系统。这个单位如同一部巨大的分析思考机器,协助美国组织、管理和推动空战,而他们的领导者就是爆出冷门的桑顿上校。四十年代初是没有电视、电脑或卫星资讯的原始世界,资讯的传达非常缓慢,桑顿上校能成功地主掌这个部门,全靠意志力不屈不挠,还有他想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在军中,控制的管道就是层层的阶级制度,桑顿着手定义他的秩序观,建立他自己的架构来行使权力。
一个脑筋清楚的士兵,绝对不敢像桑顿上校挑战梅耶和其他将领一样,单挑军中环环相扣的指挥系统,但是桑顿上校自信满溢,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强硬作风为自己树立了多少敌人,他的自信心几乎像是铜墙铁壁。多年后,他的一个同事到伦敦去,途中听到作家依恩·佛来明谈论怎样成为一个出色的莎士比亚演员,就想到用桑顿作例子。佛来明说:“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成功来自自信;你一上了舞台就知道,你打内心里晓得自己可以做得很好,那就是桑顿。他散发着自信,他的信心更鼓舞手下的人充满自信。”桑顿上校年轻时候,就立志要在世上打出名号,闯出一片天地,让他能忘记过去的卑微。从军的岁月使他深信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凭着事实和逻辑,他打败了梅耶和其他许多人;凭着事实和逻辑,他掌握了影响力。在华盛顿崭露头角的桑顿上校,早已不是德州家乡不毛之地的贝茨·桑顿。
罗斯福的新政把华盛顿变成了新耶路撒冷,一个流浪人和寻梦者的交汇点。毕竟,经济大萧条在华盛顿结束得很早,参与新政的人接管了这个城市,管理罗斯福政府新创的大大小小部门。华盛顿向来就是许多异乡人的家,现在新兴部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公务员,对于想要逃避平凡生活的人,华盛顿更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堂。这些人来自中西部和南部,来自德州和俄克拉荷马州,来自任何地方,源源不断地走出嘈杂拥挤的华盛顿车站。
桑顿上校也是其中之一,希望在华盛顿的发展中找到未来。
一九三四年,他穿着皱巴巴的黑西装、白衬衫和一双灰扑扑的鞋子,走下了巴士。新到华盛顿的人,多半都做职员的工作,坐在大办公室里。诚如某个人传神地形容:“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坐办公桌的人,在小小的纸片上写着小小的事情,对着机器录写信件,在电话里和从没见过面的人谈话。”对于单身、年仅甘一岁、多话又自信的桑顿来说,华盛顿似乎很小,要征服这个地方并不困难。
灰色童年
如果说桑顿上校喜欢控制一切,一定要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得有条不紊,那是因为父亲遗弃了他和母亲,留给他一个混乱的童年。一九一三年七月廿二日,桑顿出生在德州地势平坦、尘土飞扬的哈斯凯市。他是独子,生在一个一贫如洗的破碎家庭,没指望将来会飞黄腾达。他的人格成形期是在德州西部度过的,那里只有泥巴路,路上尽是驴子和鸡群,棉花田把原本肥沃的黑土变得愈来愈贫瘠。农夫、庄稼汉和小镇商人主宰着当地的经济,医生接生娃娃的收费也只是一个西瓜和两只鸡。
桑顿的父亲是条硬汉,没念过书,出身于德州烟不离口的下层社会,那些人成天瞎编故事,整桶整桶地喝着酒。他外号也叫“德州佬”,是个彻头彻尾的文盲,他的谋生之道就是穿上石棉衣、戴上头盔,走进炽焰熊熊的油井中,用硝化甘油把火焰扑灭。父亲狂野而遥远的影像似乎总是挥之不去。
父亲离开桑顿母子的时候,他还不到五岁,又瘦又小。他很少提起父亲抛妻弃子,但是这件事对他的伤害很大。多年来,他一直不能原谅父亲抛弃他母亲;小时候朋友都叫他贝茨,因为他不愿用父亲的外号“德州佬”。一直到他闯荡华盛顿,作风愈来愈像他记忆中的父亲,他才又用起这个名字。
桑顿胎死腹中的弟弟生下来没多久,父亲就抛妻弃子而去,再婚之后搬到阿玛利洛镇。这些年来,父亲在他的生命中来来去去。偶尔这位难得一见的爸爸会寄衣服和现金给他,甚至他的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双牛仔靴,也是父亲买给他的。有时候父亲路过镇上,会把桑顿叫到哈斯凯旅舍去见面。
他父亲对于爸爸的角色没多大兴趣,比较喜欢的是耸人听闻、油井灭火的事迹,这种嗜好使他成为新西部的传奇人物,一个浪漫、放荡的汉子,以勇猛、莽撞特立于人群,并且有超人的胆量——也有人说他半疯半癫——是不怕死的人,才会拿着硝化甘油走进熊熊烈火里去。他在油田的名声,几乎可以媲美一百年前亚利桑那州矿区的传奇人物,在欧凯科罗一战成名的怀特·厄普。老桑顿在一九四九年去世,死得像他生前一般莽烈——他在阿玛利洛的汽车旅馆,被一个搭便车旅行的男子用老桑顿自己的手枪痛殴至死。这名男子宣称他撞见老桑顿和他廿二岁的妻子同床共枕,一丝不挂。双人床头的墙壁上,血迹溅了三、四尺高,桑顿五十七岁的父亲被人发现赤身裸体躺在床上的血泊中,脖子上紧紧绕着他自己的衬衫和毛巾。涉嫌的凶手被以谋杀罪起诉,经过漫长的诉讼,最后获判无罪。
母亲的梦
有时候他和母亲出门,两个人身上带的钱只有十来分。他的母亲闺名叫莎拉·爱丽丝·贝茨,是个宗教信仰虔诚的女人,受的教育不多,身兼严父慈母的角色。她管不了桑顿的父亲,却影响了桑顿的一生。她短小圆润,一头黑发和蓝眼睛,桑顿如果犯错,她会毫不犹豫地抽出皮带打得他死去活来。但是桑顿尊敬她。她灌输他要自食其力、出人头地,用单纯的乡下价值观念对他耳提面命,这些观念后来都成为他生命的基石。“做人说话要算话,”她总是这么说,“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一个人的信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同样的教训他是听了又听。他十一岁的时候母亲改嫁给路易斯,路易斯是在州政府做事的兽医,在各大农场上诊治牛群、马匹,以及检验肺结核。桑顿多了个继父,家里后来又多了同母异父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桑顿的自我意识并非来自与他疏远的父亲,而是得自他专横的母亲。她不许桑顿再走上他父亲的路,做个浪荡子,她把——自己无法达成的愿望,都寄望在儿子身上;桑顿一定会出人头地,一定会做出一番大事业来,她这样告诉自己,也这样要求儿子。后来桑顿开始实现她的梦想,她的长子就成了家里每一个人的楷模,她成天对桑顿的三个弟妹洗脑,然而这三个孩子都达不到她的期望。她的小儿子艾伦被逼得受不了,逐渐与家人疏离,最后喝氰化物自杀,他的妻子为了阻止他,情急之下用手枪朝他的手开了一枪,还是挽回不了悲剧。
桑顿的家平凡无奇,是一幢老式的两层楼木造房子,虽然三餐无虞,但是手头总是不太宽裕。十几岁的桑顿就已经表现出勤劳、自食其力的个性,这也是后来他赖以攀越巅峰的力量。夏日里,他清晨四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囫囵吞下一点早餐,然后搭便车到五里外的农场工作,一个小时赚十分钱。母亲会帮他准备饼干夹上一两片熏肉,再加一罐豆子当午餐,就打发他出门。他总是和朋友约翰·金伯洛一块儿上路,农场就是金伯洛的爸爸开的。“桑顿才不是什么乖宝宝,”金伯洛回忆道,“万圣节的时候,他会把仓库搞得天翻地覆。有时候看到男生开车载女生兜风,我们会拿臭鸡蛋丢他们,如果他们停下车来,我们就去泄他们轮胎的气。”这是乡下孩子典型的恶作剧。
事实证明他的拳脚功夫的确有两下子,有一回一个小混混想搅和他跟女孩子的约会,被他打了个屁滚尿流。好斗的桑顿决不容许任何人占他的便宜,不论他胜算有多小,凭着他的双手,他保住了女朋友的名声,也顺利地做起小生意,在后院里养鸡卖鸡蛋,甚至还和一个朋友一起酿私酒来卖。
对任何有野心的人而言,哈斯凯市就象是个监狱。日常生活就以光秃秃的广场为中心,一旁点缀着典型的地方法院,就是那种有个高耸的尖塔和一口大钟的建筑。广场四周有几家破旧的商店,卖些五谷杂粮和五金杂货。这些年来他母亲老是做着同样的梦,她不断地重复说给其他孩子听,他们才知道她对桑顿的寄望有多高。在这个梦里,她儿子开着一辆黑色敞蓬大车,缓缓走在一条宽敞的林荫大道上,路边挤满了上千,甚至上万的人,在人行道上对着笑容可掬的桑顿微笑、挥手、欢呼,梦里的桑顿可不是待在一个肮脏的小镇,四处找不到工作。
前进华盛顿
一九三一年桑顿和四十六个同学从哈斯凯高中毕业,此际,美国正碰上经济大萧条。哈斯凯市有两家银行关门,农夫也纷纷卖地还债,他继父把全家搬到路伯克,桑顿就在当地的德州工技学院念工程,后来改念商。他母亲收了几个房客赚房租,好让他继续升学,但是他念完二年级就退学,搬回哈斯凯,跟朋友布福德·柯克斯合开一家小小的朴利茅斯汽车经销店。桑顿——想到用期票方式卖车子给农民的主意,等他们收成以后再付款。他却没料到,许多农民早就欠了银行一屁股债,虽然他是很优秀的推销员,但是他的客户信用太差,结果经销商店开张没多久就关门大吉了,最后还是父亲伸出援手,帮他解决了财务困难。这时候,桑顿决定离开哈斯凯。他向哈斯凯的一家银行借了五十美元,再跟朋友借了几块钱,就上了灰狗巴士,直奔华府和罗斯福的新政府。对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穷小子来讲,华盛顿是权力和进步的象征。哈斯凯、路伯克这些小地方听到的消息,总是说政府不断在扩大,新的机关、部门和委员会不断成立,每个单位都有几百个工作机会,等着新来的人。
然而,在那个时候,华盛顿是一个讲关系的地方,就算是想在一个机关里找个什么不起眼的工作,也得要有门路。亏他早就想到这点了,桑顿到华盛顿之前,已经拜访过同乡的新科国会议员摩尔·马宏。他走进科罗拉多市马宏的办公室,向他自我介绍,并请他写一封介绍信,好让他带着到华盛顿去。马宏帮他写了一封短简给“公共事业振兴署”,可惜他们暂时并不缺人。
吃了很多次闭门羹之后,他不禁怀疑,他是不是根本不该离开德州。他没有想到竟然会有这么多人到华盛顿来找工作,报纸上说,每年都有五万人涌入华盛顿。借来的五十美元,现在只剩下几块钱而已。他约好要去“农业协调署”面谈,那也是一个无聊的官僚机关,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
天气倒不是刺骨的冷,华盛顿向来很少有刺骨的冷天气,而是那浸入骨髓的湿冷,让人直打哆咦。如果桑顿的母亲在这一刻看到他的话,发觉他不是在白宫的前厅,也不是在摩尔城的鸡尾酒会,而是在哀求人家给他一份基层职员的工作,她可能要失声痛哭。
“看见外头那张长板凳了没有?”桑顿说,一边朝着窗户点点头。“假如我拿不到这份工作的话,我今天晚上就只有睡在那里了。”
他争取到那份年薪一千二百六十美元的工作,头衔是“雇员”。但是两个月后就离开了,因为他在罗斯福政府的另一个机关找到性质类似的工作,但是薪水多了一成五。他发疯似地拼命工作,晋升为“助理统计”,又换到另一个政府机关,最后到一九四一年他跳槽到国家住都局,职称是“统计师”。从一九三五到一九四一的六七年间,他发狂地工作,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往上爬。话说回来,不管他做什么事,都是为了控制他生命里的每一点每一滴,包括他对弗洛拉·蓝妮的追求。
良妻美眷
在那个时代,世界完全受男人控制,美国女性充其量不过是第二性。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婚后愿意待在家里做个贤妻良母的女孩子,才是最有吸引力的女人。如果女人无法在丈夫的梦想中找到慰藉,至少得懂得分享丈夫的期望,她们自己的梦想则丢在一边。当然,战争会把上百万的妇女拉进经济活动里,使女人头一次了解到她们的能力并不是仅仅局限在扫地煮饭。但是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她们很快又会重拾比较传统的家庭主妇角色,男人努力工作,而女人就扮演男人的伴侣兼知己。
桑顿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和别人没有两样,他跟当时的许多单身汉一样,希望妻子扮演家庭的轴心,两个人一起建立家园。他已经找到这样一个女孩子,那就是弗洛拉。弗洛拉的姐姐伊莉莎白,是桑顿在住都局的同事,有次她在家里办个小聚会,桑顿跟弗洛拉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弗洛拉身材窈窕,声音低沉,有着修长的双腿和蓝灰色的眼睛。她也念过德州工技学院,但是比桑顿高一班,因此他们在学校里没有正式见过面,而且她也决不会跟低年级的学弟约会,在那个时代没有人会这么做,弗洛拉更是不会,不管桑顿再怎样沉着、再怎样自负。但是桑顿记得她,因为弗洛拉认识几位他教会里的弟兄,她还在第一卫理公会教堂的唱诗班里唱过诗。母亲的鞭策迫使桑顿加入教会的青年团,成为周日礼拜的常客。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弗洛拉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特殊的气质。她倒不是认为他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而是他的忠诚和个性使她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我看到端正的,”她说,“一种不拘泥于传统的个性,让人觉得很新鲜。他呀,怎么说呢,就是与众不同。”有一天晚上,桑顿不知怎么聊到科学这个话题,一直讲个不停,告诉弗洛拉克服地心引力的可能性,以及可能的影响。约会的时候谈科学实在有些奇怪,她认识的男孩子没几个会谈起这些的,不过那就是桑顿,永远出人意表。
“谁说要结婚的?”她笑了起来。
“当然,我是要娶你的,”他说,“但是要等到我们有钱的时候才行。”
“多谢你的恭维,”她回答说,“但是我可不想为了配合你或任何人的生涯规划,在这里痴痴地等。”
然而桑顿却已经下定决心。他们后来对这个问题还是争论不休,但是他每个星期六还是会搭火车到纽约,星期天晚上再回去。星期六晚上表演结束以后,他会到四十九街和第六大道间的中央剧场,到剧场后门去接她,然后两个人就在纽约市区闲逛。那时候他年薪才一千八百美元,没有闲钱去做奢华的娱乐,不过他知道她希望他来纽约陪她玩,有一次他还大手笔请她在洛克菲勒的彩虹厅跳了一个晚上的舞。
双方很快就认真起来。为了去华盛顿找桑顿,弗洛拉没有参加最后的彩排。一个星期之后,她就从演出名单中被除名了,桑顿又再一次称心如愿。他们在聚会上初逢大约满一年以后,就在一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缔结连理。周未他们开着桑顿的老雪佛兰,到佛吉尼亚的泻兰多河谷玩一趟,就算度了蜜月,星期一早上,他又回到住都局的办公桌前上班。
他们在爵禄街上找了间一房一厅的公寓。弗洛拉在拉什洛普公司的婚礼部门找了一份工作,同时还在国会山庄的信义会唱诗班兼差唱诗。晚上,桑顿就跟华府各机关里不想一辈子当职员、打字员的人,一起到摩尔华盛顿大学上课。
青云路
桑顿因为精于数字,在住都局步步高升。他写了一篇低成本住屋的研究报告,内容清晰、思虑周详,博得上级的关注。摩尔华盛顿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介绍他去找作战部的罗维特先生,这位教授很欣赏桑顿,又认识罗维特,他认为这两个德州佬可以搭上线,这正是桑顿迫切需要的突破。战争的风暴已经吹进华盛顿,希特勒入侵波兰,英国加入战争,法国已失守,巴黎沦陷,德国空军大规模空袭伦敦和英格兰乡间,投弹如雨。罗斯福上了广播节目“炉边闲话”,呼吁援助英国,虽然国会议员批评他是好战分子,然而商店已经纷纷在窗口挂起送爱心到不列颠的标志,征求衣物和其他急需品。国会无异议通过恢复征兵。
桑顿早已取得后备军人委任令。只要战争一爆发,他立刻就会加入。罗维特后来和桑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几乎像是他的父亲;这时候,罗维特已经是华府政坛要人,一旦战争爆发,他随时可以担当重任。他身材硕长、风度翩翩,在一次大战期间担任轰炸机驾驶员,现在官拜作战部副部长,正希望以新的观念,有一番新的作为。桑顿攀上这层关系,约好去拜会老成世故的罗维特,罗维特的办公室在宪法大道的旧军火大楼。桑顿等了整整半个小时他才出现,穿着蓝色双排扣亚麻布料西服,一件有字母组合图纹的白色衬衫和一条蓝领带。
罗维特的坦率令桑顿大感意外。他告诉桑顿说,光是一张陆军航空队的组织图,就能让人看得头昏眼花。“这张图简直就像一盘意大利面”他笑道。罗维特预见航空队会大事扩张,因此更需要掌握部队的情况,做好确实的纪录。他和桑顿初见面,就发现这年轻人并不畏惧权威,他们谈论着统计和数字,他发觉眼前这个年轻人天生精于数字,具有分析的头脑。
桑顿问他:“副部长先生,我们费了许多心思侦测敌人情报,但是对于友方的情报,我是指有关我们自己的可靠消息,又做了多少呢?”
这个问题引起罗维特的共鸣,他一直在向航空参谋处调查他们有多少飞机、零件、驾驶员和维修人员,万一美国卷入了欧洲的战事,航空队需要有什么准备才能发动战争。罗维特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初,把桑顿安插在航空队的规划部门,让这个统计规划师主持一个国民兵组成的小组,负责支援各个幕僚部门的工作。桑顿执掌的不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却为他开启了——一扇窗,让他见识到航空队内部是多么的混乱无序,也让他领教到事实和数据对于效率是多么的重要。
几乎每天都会有人走进办公室,查阅航空队的计划书和飞机的需求,但是他们得到的答复却每天不同,因为航空队根本没有确切的计划。桑顿最后在作战部一个罕为人知的小组里找到一个人,他手上有一份计划书,说明每个月要训练一万两千个驾驶员。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桑顿问他。
“凭空杜撰来的。”
桑顿闻言失笑,接着追问他:“那么,这跟我们的飞机采购计划或者是扩充计划有任何关系吗?”
“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说,“有的话,也是纯属巧合。”
事情的真相是,每一个幕僚部门,无论愿不愿意,都只能各自杜撰计划,一再捏造数据。所有的资料都对不上,也凑不起来。这种做法用来造反还可以,想发动战争连门都没有。
总部号称有十几个机构在负责资料的统计,然而多半的时候他们都是在争论谁的数字才是正确的,航空队指挥官亨利·阿诺德通常跟四个不同的幕僚部门要相同的资料,然后挑出最接近的两组数字,就当作正确的答案。还有一位航空现阶段将领说他反正不需要任何资料,因为他都是靠私人关系来运作部队的。“这太荒谬了,”桑顿吼道,“你们身上有五亿美元的投资,任何一个小小的战斗单位都不可能这样运作,更何况是整个航空队。”
开战
从那时候开始,工作快速地扩展开来。桑顿一向就喜欢长时间工作,现在弗洛拉和他碰面的时间比以前更少了。整个华盛顿生活变化得非常快,政府机构的楼顶都架起高射炮,而在嘎吱作响的木造军火大楼,也就是作战部总部所在地的外面,站岗的卫兵还拿着一次大战时代的旧步枪,枪上装着刺刀,总部里面本来只穿褐色呢夹克、灰长裤的人,现在都换上了军服,挤满了破旧不堪的军火大楼。华盛顿的官场上,现在出现了新伦理,因为在紧急备战的混乱情势中,新的英雄随日而生、随日而垮,谁都不确定谁会被看中或被炒鱿鱼。
桑顿花了可观的时间去搞清楚哪个将军得敬而远之,哪个该投怀送抱。不过多亏了罗维特的指点,他经常都能窥得面具.. ——后头的真面目,预先就知道该如何去应对。在战争初期的混乱中,罗维特逐渐成为他的恩师兼保护人。
对桑顿来说,他的工作步调已经几近歇斯底里的地步,处在长期的压力下,连青春痘都冒出来了,他的工作量之大远超过常人,还得想尽办法,追踪各个计划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工作压力加上作战部里明枪暗箭、条件交换的那一套,逼得他更加狂热,还有很多人并不热衷交出手上的资料,免得被他抢走了权力地位,这些人他全都得提防着。
只有等到晚上,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才有机会坐下来好好思考。房间的天花板还有水渍的痕迹,门口对着另外两间办公室,里面挤满了桌子,统计师就在那儿为企画师核对数字。每天晚上他会找几个他的人,聚在一块儿交换意见,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
他总是说:“知识就是力量。而在这片混乱中,我们将是唯一有知识的人,其他人只能瞎猜。”
他们都知道他说得很对,但是要搜集和查证资料,最后根据这些资料来做决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桑顿看过也听过很多人为了应付需索而杜撰事实,结果就是一片混乱。
乱中求序
在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后,军火大楼弯曲的走廊里,只见军官上上下下地忙个不停,每个人都在说:“一定要想想办法。”还有人明白表示,希望能调到战场上,离开这片无可救药的混乱。桑顿后来才说,当年他很可能把美国赢得战争的机会廉价地舍弃掉,不过他还是把疑虑留在自己心底;无论如何,战争爆发使大家感受到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并改正缺失。
桑顿顺势打入这个真空状态。他力促罗维特支持航空队的紧急训练计划,否则航空队终会毁灭在一堆假设和半真半假的资料里面。一九四二年三月间,阿诺德将军宣布陆军航空队总部要进行重大改组。桑顿奉命出掌“统计管制处”,在组织系统上是盖茨上校“管理控制局”下面的一个小单位。盖茨是老一辈的人,毕业于西点军校,因为身形瘦削,被人叫做“饿死鬼”。后来桑顿靠着他,得到必要的保护与支援,毕竟他当时只不过是个廿八岁的少校,服务不满一年,又没受过一天真正的军事训练。
然而桑顿可是别有所图,罗维特的远见、信任和支持,可以让他达成目标。他们预见一个完整的资料网路,把统计管制官派驻到全球各地的航空队指挥中心,负责搜集人员和装备的资料和数据,并加以整理、分析。他们好比公司的主计人员,他们的报告将透过一个平行独立的指挥体系,源源流进空军总部,而发号施令的就是桑顿。
这个德州的退学生,很快就会挑起大梁、掌控权力,在他的生命中首次担当大任。对一个从小就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人来说,这个工作有着令人着魔的吸引力,在这非常时刻,资讯情报就是力量。桑顿因为有这一点认知,使他脱颖而出,而且旁观者清,他比那些一心只想维持既有地位的当局者看得更清这是一个无比远大的野心,但是桑顿受母亲影响,一心要闯出名号,做出一番事业。他的机构需要什么样的人呢?他想到的答案再次证明是神来之笔,要经营桑顿心目中这样大规模的一个系统,他的人马必须要有相当的官阶,才能引起别人的重视,中士、下士绝对不够,他需要受过特殊训练、具有地位和权威的人。罗维特最清楚关系的重要,以及精英主义的力量,他建议桑顿去找哈佛商学院院长,探听他是否有意主持训练计划,培训一批精英军官。桑顿带着罗维特的建议和支持,在一九四二年四月搭上火车,前去拜访这个他在德州时只闻其名的名校,就在火车上,他构恩了他事业生涯中最好的一个计划。